
時代瘋魔,文本成活——陳雪《親愛的共犯》影集版確定!
有沒有這個可能:你抓到了犯人,卻不希望是他們?山上一間純白的高級住宅,山下一間不見天日的育幼院,解謎如解夢的警探,犯案如自白的共犯,案件涉及十幾年,十七人全員嫌疑,被害者不一定乾淨,但加害者一定有問題⋯⋯?為了愛,我們下地獄,一層、一層、再一層地走下去。———————————————————「我一直想寫暴行,施加於人卻無形的暴力,例如控制與剝奪。」——陳雪———————————————————現代社會派推理最高傑作!第十五屆台北國際書展大獎小說獎.陳雪《親愛的共犯》(鏡文學出版),日前售出影視版權後,正全力進行影集版的大型影視化工程,而純文學出發,行經了同志文學、愛情散文和人妻日記,一路走到了犯罪小說的惡女陳雪,作品多次獲文學獎,影視化歷史更是閃閃發光。———————————————————《蝴蝶》(印刻出版)改編之香港電影《蝴蝶》,獲台灣金馬獎最佳新演員獎、最佳改編劇本獎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獎,香港電影金紫荊獎最佳女主角獎、最佳男配角提名、最佳女配角提名,巴黎女同志和女權主義者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獎,另選為香港同志影展開幕片、威尼斯國際電影節國際影評人週閉幕片。「★★★★★★★★★(9/10)」——《IMDB》、「非常好的角色研究。」——英國《螢幕週刊》。———————————————————《摩天大樓》(麥田出版)改編之中國騰訊影集《摩天大樓》,獲豆瓣8.2高分,中國初心榜年度五大青年導演提名、年度傑出平台型製片人提名,中國華鼎獎年度電視劇滿意度調查百強第13名,中國指尖傳播影響力報告年度最具影響力短劇集獎,中國金骨朵網路影視線上盛典年度品質短劇集獎,章子怡、郭富城、林心如、徐崢——發文推薦。「★★★★(4/5)」——《豆瓣評分》、「敘述手法獨特清晰。」——章子怡(演員、電影製片人、導演)。———————————————————時代瘋魔,文本成活,陳雪第③部影視化作品——跌入人間荒涼、焚燒人心火花、思辨人類罪罰之《親愛的共犯》,影集版全速開發中,我們一步、一步、再一步地走下去。
+ More
人間哪有凡爾賽 看職業小說家甩斧頭——楊隸亞評陳雪《親愛的共犯》
夢幻豪宅殺人案 很久沒有這樣的感覺,捨不得讀完一本小說。陳雪近年曾說要完成小說三部曲計畫,分別是一座大樓,一座城市,一座小島。從已出版的長篇小說《摩天大樓》(2015),《無父之城》(2019)來看,小說家真的說到做到,《摩天大樓》讓讀者窺見水泥森林裡都市人類內心的孤獨荒涼,《無父之城》走入小鎮尋找身世命運與歷史記憶流變。這次,最新長篇小說《親愛的共犯》(2021)小說家的眼睛同樣凝視著「空間」展開,豪宅vs育幼院,富有vs貧弱,空間的對立感所營造的階級群像也不停指引(誤導)讀者,讀至最末章仍在真相邊緣打滑繞圈。《親愛的共犯》陳雪 著出版日期:2021/1/29《親愛的共犯》全書有四章,分別是:夢中人、沉睡者、追擊者、守護者。在懸疑小說的推理架構底下,透過整部小說的靈魂人物——女警周小詠,走進豪宅與育幼院,撥開層層雲霧尋兇辦案,也透過她的雙眼顛覆傳統定義的空間價值、家庭組成、愛情觀念。這部小說該要垂直去看,看山坡上,看市中心,還有,看流浪天涯四方,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小說開始就花費大量的篇幅做空間造景,故事出現兩棟強烈對比的房子,一棟是山坡上的育幼院,另一棟是位於市中心黃金地段,別名為「白樓」的高級豪宅。育幼院裡的孩子三餐僅是溫飽,多人共用狹窄的客廳廚房,煮飯打掃雙手萬能,雙層上下床舖,一張床還得擠著兩個孩子,他們用自己的塗鴉繪畫和生活照片裝飾點綴牆面,手牽手甜蜜的像真正的家人。而另一棟「白樓」豪宅,從設計動線到建築美學,清水模構造現代主義,以為安藤忠雄到此一遊,兩旁盡是獨家展品,搭乘電梯往上升,一層一戶,司機外傭阿姨服務到位,採光入屋,卻不入心,滿滿的冰冷。小說家陳雪以豪宅主人張大安最疼愛的二兒子張鎮東被綁架勒索為故事開端,展開一連串警方與殺人犯的諜對諜攻防戰。台灣的宮部美幸二月上旬,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的陳國偉所長於「開房間」(ClubHouse)app發起『台灣宮部美幸,襲來!?』的類型小說討論,他指出以下概念:日本一直有『國民作家』的傳統,最年輕的一位,正是多數讀者相當熟悉的宮部美幸,而台灣作家陳雪近年交出的長篇小說作品,如《摩天大樓》、《無父之城》到《親愛的共犯》,書中處理角色人物與社會議題的手法,都讓人聯想到宮部美幸。老實說,閱讀《親愛的共犯》過程中,陳雪處理死亡與掩蓋秘密的指向,比起「技術指向」,更多的確實是一種「情感指向」,讓我有那麼一瞬間想起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在《嫌疑犯X的獻身》裡面所創造的「愛的犧牲」。多年前,《嫌疑犯X的獻身》究竟是否屬於「本格派」推理小說,曾引起不少討論。小說裡的愛意,一個人可以為世界上另一個人付出到什麼程度?比起數學推理,擺在面前的是巨大到令人惶恐的愛。不過,X一書確實更偏向「時間秘密」的機智解謎,《親愛的共犯》雖然也製造出類似「時間秘密」的手法,卻不是通往真相的唯一路徑,比較像是聲東擊西,用來阻擋、轉移人們視線的障眼法。如果說推理可以拆成兩條思維,一條是合理,一條是合情,《親愛的共犯》更接近後面那條「情之路」,情多於理,刻畫人性多於解謎刺激。這並非意味小說在推理結構不夠慎重緊密,而是比起武功技藝,或許小說家更期待讀者能夠把人物的內心世界看清楚。當讀者依循小說家拋出的各種線索,條件紛紛指向「群體犯罪」,甚至就要大膽斷言這是一場類似「東方快車謀殺案」,一人捅一刀的大團圓套路犯案。最後一章,陳雪再度讓你大吃一驚,事情完全不是看上去那麼單純。因此,要細講起來,比起本格派的出手,陳雪在《親愛的共犯》所要展現的,確實更接近宮部美幸那般,往「社會派」的方向傾斜,比起享受解謎鬥智的刺激感,更多是一拳打在你心臟胸口上人性試煉的重擊。看職業小說家甩斧頭村上春樹固定慢跑,宮部美幸喜歡打電動,陳雪則是每天吃完早午餐後,下午固定寫長篇小說,1500至2000字左右,每週規律做瑜伽,晚上深蹲加追劇。過年期間,聽說只休除夕跟大年初一,每天都寫,從不間斷,高度自律的她曾表示,當日小說進度完成之前,絕不開臉書。我想起村上在《職業小說家》裡曾提及:『小說家的賞味期限——頂多十年左右吧。超過這個期限之後,就必須有更大的、永續的資質,來代替頭腦的靈活了。』他還舉例小說家的進程是三把銳利的刀,剛起步的小說家有「剃刀的鋒利」,往後能演變成「柴刀的鋒利」,最後抵達「斧頭的鋒利」。能夠順利轉換下去,即是戰勝自己存活下來的小說家。回想陳雪的第一本小說集《惡女書》(1995),時至今日已過26年,如今的陳雪,是否已走到村上春樹在職業小說家分類裡,傳說的「斧頭刀」等級呢?本次新作《親愛的共犯》有一段描述,特別動人:『當時他們四個人,曾經說好永遠不分離,好像這世界上只剩下了他們,所以他們必須好好地守護著彼此。在那片山坡上,李安妮說過她將來要當歌星,林曉峰說他要當太空人,崔牧芸呢?她說她想要當護士,只有陳高歌,什麼願望也不肯許,或者他想過了但他不肯說出來,當大家鬧著要他說的時候,他就說了,「希望我們永遠是一家人。」這樣自立自強,只能依靠意志力建造夢想的孩子,讓我想到陳雪的短篇小說集《橋上的孩子》,裡面有一個家庭經濟陷入困境,被生命逼迫長大的少女。我也曾在不同的文學場合,書展講座或文學營聽過陳雪提起一段故事,那是關於小女孩在一棟如同迷宮的旅館裡尋找母親的故事,母親就藏在某一個號碼的門背後,這段尋覓之旅也是尋愛的渴望、孤寂、脆弱。從前,在迷宮旅館尋找母親的小女孩,在夜市擺攤叫賣衣服或批發手錶送貨,夜裡抓緊時間瘋狂寫小說的少女,赤足踩刀一路走來,如今成為職業小說家陳雪。她不再需要取下身上的羽毛來當作故事題材,一出手就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本文作者楊隸亞一九八四年十月生,台北人。東海大學中文系,成功大學現代文學碩士畢,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散文評審獎及懷恩文學獎、桃城文學獎等其他獎項。作品散見各報副刊、《印刻文學生活誌》、鏡傳媒等。
+ More
哪一種才算是家,的推理——張國立評《親愛的共犯》
大部分推理小說總是在死了一個人之後開始,忽然想起大導演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代表作有《銀翼殺手》、《異形》、《王者天下》、《黑鷹計畫》、《神鬼戰士》)的《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關於塞爾瑪與路易絲兩個女人的故事。她們本來過著平常日子,塞爾瑪是個家庭主婦,有個易怒的老公,路易絲則是餐廳服務生,有個不太確定關係的男友。這天,天氣不錯,路易絲心情很好,邀塞爾瑪出去玩,塞爾瑪不敢對丈夫說,可是她決定該出去走走。所以這也是關於旅行的故事。旅途永遠不可能平順,在酒吧外,塞爾瑪險些被男人強暴,路易絲一槍幹掉那男人,旅行變成逃亡。接著塞爾瑪遇上帥哥騙子(布萊德.彼特飾演)而被偷走了她們所有的盤纏。她覺得對不起路易絲,持槍搶了商店,這下子她們再成了搶匪,從調查局到州警動員大批警力的四處圍捕。記憶最深刻的是當塞爾瑪被布萊德.彼特偷走了錢,那是上午,其他人仍過著正常生活,可愛的塞爾瑪卻成了搶匪。她的搶,純粹為了繼續旅程,繼續她終於明白的「存在」。原以為挺絕望,但塞爾瑪終於從丈夫的束縛裡掙脫出來,路易絲也了解男友對她的真愛,「末路」充滿歡樂,她們享受每一刻。《親愛的共犯》陳雪 著出版日期:2021/1/29法國著名的推理小說家奚默農(Georges Simenon, 1903-1989)寫過一個短篇小說《警探回憶錄》(From Maigret’s Memoirs),故事的主角是名巴黎老警員,他穿釘鐵片的大頭靴天天巡邏於市區,之所以穿大頭靴,是一來警察的薪水買不起好鞋子,二來每天得走十三至十四小時的路。他說,警察的工作和街頭妓女差不多,都有雙得走上幾英哩柏油路的鞋子與疼痛的腳踝。他的工作當然是破案,長官交給他一把凶刀,設法找出凶手,於是老警員帶著凶刀出門,九個月後在某家文具行問出凶刀是這裡賣出的,而老闆還記得買刀的人。他靠堅持與耐心破案。奚默農透過老警員的眼睛帶領讀者看那時候的巴黎,看著初進城的青澀少女隨歲月變成目光渙散的老妓女、看著火車站內找機會的盜賊。推理小說便在生活裡尋找蛛絲馬跡,設法找出答案。奚默農寫,當時巴黎警察兩個特徵:穿大頭靴是因為待遇低,這種鞋子耐走;留大鬍子的起源不明,但大多數年輕人加入警界就是想留大鬍子,覺得酷。讀者隨著大頭鞋同時也進入警察的日常生活,人物像在定格的畫面停留好幾分鐘,然後突然間走起路、說起話。雷蒙.錢德勒的《大眠》,嫌犯卡門小姐到偵探社找偵探馬羅,他們之間有段對話。「幹這一行(偵探),如果你誠實的話,賺不到什麼錢。如果你有門面,那表示你賺了錢──或者準備撈一筆。」馬羅這麼介紹自己的辦公室。「噢,你誠實嗎?」卡門一邊打開皮包一邊問,她從一個法國製琺瑯盒裡取一根菸,用一只口袋型打火機點火,然後把琺瑯盒和打火機丟回皮包,任由皮包開口。馬羅回答,「誠實得很痛苦。」馬上了解馬羅是什麼樣的偵探,了解他的日子不太寬裕,而找上門的女客戶則有錢到滴油。以《後車廂輓歌》(Trunk Music)創造出著名偵探鮑許的麥可.康納利(Michael Connelly)用另一種方式表現偵探的工作,不再古典時期的優雅,非常冷硬時期的寫實。鮑許談到偵探的工作:「有個雕刻家,當別人問他怎麼把一塊花岡岩變成一尊美女雕像?他說他只是剔除不屬於女人的部分。我們現在要做的也是一樣。」偵探得拿著小鑿子對花岡岩一點點的敲,不能太用力,萬一敲太多,黏不回來的。好看的推理小說必從人性著手,一如巡邏警察偵破殺人案於他的日常、靠他的每一步,這是他的人生。一如拿破崙部下說:「皇帝打勝仗靠的不是我們的刺刀,是我們的腳。」陳雪的《親愛的共犯》一方面女刑警周小詠追查殺死富商二子張鎮東的凶手,一方面作者追查到底「家」該如何定義?真正的家在哪裡?為此,陳雪詳細介紹豪門張氏一家三代居於一棟低調豪宅白樓內的生活點滴,大家長張大安原想這樣能凝聚家人的感情與力量,卻忘記錢畢竟是萬惡之源。錢未必可怕,錢帶來的勢利與階級才可怕,稍稍處理不慎會帶來大禍。這三代糾葛不清的恩怨情仇便是故事的大背景。同時,作者暗示:少了愛,這是家嗎?另一群成長於育幼院的年輕人,他們未忘記當年以院為家培育出濃郁革命感情,彼此關照,當其中一人有難,其他人不顧一切的設法為之解脫。作者再暗示:這樣的感情不算家嗎?透過女刑警的不懈的偵查,她帶出一個人物串接一個人物,帶出每個人的故事,像是拿破崙手下的法國大軍,所有人物奮力的前進,抵達戰鬥位置,組成綿密的戰列,等著作者下最後的攻擊指令。《親愛的共犯》追查的是我們究竟該認同哪一種的家。人生百分之九十處於大多數人認同的軌道上,像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在《黑暗,帶我走》(Darkness, Take My Hand)裡說的:「他們在人生中載浮載沉,如同浮在熱水上的塑膠鴨,有時會翻側到一邊,等到有人把他們扶正過來,他們又回復先前的載浮載沉。他們不吵架,也沒有真正的熱情。」張鎮東對家人施暴,對事業、對家庭只有要求而不無付出,家裡的親人設法掩蓋事實,像把翻側的塑膠鴨扶正,他們有錢有地位,卻不知道自己失去了熱情,那麼鴨子的倒或正有何區別呢?女警探周小詠找出凶手,然後呢?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里塔斯這麼做結論:「尋找真相時,要對不可預期之事有所準備,因為真相總是如此難尋,而且總是在你尋獲時困擾著你。」想到某本小說裡說的:「問題不在於你能不能找到真相,而在你能承受得起真相嗎?」本文作者張國立知名作家/美食、旅遊達人/擅長推理小說、歷史小說等。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曾任《時報周刊》總編輯,得過國內各大文學獎項與金鼎獎,文筆既可詼諧亦可正經,作品涵蓋文學、軍事、歷史、劇本、遊記等各類題材。近期作品:《乩童警探:偏心的死刑犯》、《炒飯狙擊手》、《金陵福 史上第二偉大的魔術師》、《海龍改改》、《一口咬掉人生》、《戰爭之外》、《鄭成功密碼》、《張大千與張學良的晚宴》、《棄業偵探:不會死的人,一直在逃亡的億萬富翁》、《棄業偵探01:沒有嘴巴的貓,拒絕脫罪的嫌疑犯》、《偷眼淚的天使》……等。小說《炒飯狙擊手》已售出北美、尼德蘭(荷蘭)等國外版權。
+ More
愛的有罪論──蔣亞妮讀《親愛的共犯》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裡,寫下:「我們在沒有被忘記之前,就會變成一種媚俗,媚俗是存在與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點。」陳雪的新作《親愛的共犯》逼近的核心,與它相近。與其說,這是一部懸疑小說、推理小說,其實它更是藉著一場綁架失蹤案、借道小說中住在「白樓」裡外的眾人,將視線投向「媚俗」世間。像是以燈探照,什麼是好、什麼是愛,你的心真的為此震動嗎?《親愛的共犯》陳雪 著出版日期:2021/1/29與前作《無父之城》相同,故事始於一場失蹤。這一回,住在「白樓」裡顯貴的張家三代,二子張鎮東忽然被綁架,刑警周小詠展開調查。嫌疑者有財富、有愛情,當然也有妒恨,人類究竟會被什麼驅動?當我們關心一個社會案件、當我們為了家人與愛情付出、傷痛、流下眼淚時,要怎麼看待每一滴眼淚?眼淚,總有兩種,第一種眼淚,是出於自己與對方的關係;第二種眼淚,卻是因為彷彿能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同悲憫共感動,如此美好豐沛,流下的淚。兩種眼淚,都是愛,或以為是愛。這也是米蘭·昆德拉告訴我們的:「地球上人的博愛將只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如果可能,請把這本小說裡所有的眼淚與選擇,看作第二種。只因為,這個世界目前的眼淚,都更貼靠後者。複調之式神陳雪的小說總像是課堂裡沒教的文學核心。奇技淫巧與理論形式,那些可以被書明、曾經被論述的典籍,先變作了小說作品(work),再變成我們所見真正的文本(text)。從作品到文本的逸變,是一種精神視線,作品是可見的,文本是不可見、不可被計算與評價的;作品會佔據空間,文本則是一座方法場,我們只有透過創作過程,才能檢驗文本。曾有個被單一化到極致的人物,那位像是一生只說了一句「作者已死」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其實他所知更多:「文本不只是符碼、可見的物件,更是烏托邦、不可見及一個可流動的過程。」如此看向陳雪小說的軸心,尤其到了《摩天大樓》與《無父之城》後,更能理整出她小說的特長之處,課本裡、理論上、簡而化之的一個名詞:「複調小說」。西方世界,從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威廉·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的小說到《冰與火之歌》;東方與之相對,亦有《羅生門》及上溯至《紅樓夢》、近身如湊佳苗小說般的複調藍本。於陳雪的小說中,不管是此本《親愛的共犯》裡,間次地以失蹤者張鎮東身邊之人開章分述,從引夢辦案的刑警周小詠、生於微處的張鎮東妻子崔牧芸、張鎮東的大哥大嫂,到白樓裡的管家陳嫂、外傭阿蒂⋯⋯全都成了陳雪指點江山的各種樂音。一如她在《附魔者》裡,似以魂力捻出燭繩般,點燃所有在愛中的不同傷者與叛者⋯⋯直至《親愛的共犯》,讀者終於可以篤定知曉,小說家完全自知她與她的小說之技,有著如陰陽師與式神般最強大的契約術法,不論是複調、懸疑與人性,她都握於掌、曉於心。大象灰色的夢遊者小說和愛情總是相近,最近之處,是明明知道所有的道理、做好一切準備,卻還是寫不好一本小說、談不好一場戀愛。這便是「複調小說」一詞,在課堂外的核心,在陳雪手中的別樣,更是陳雪在經過了幾年的文學高強度寫作計畫(字母會)後,意外地,將她的自我與小說濃淡度調低,從墨黑漂成了大象灰。小說中幾次以顏色寓階級,先是「白樓」那難以言說的白之綜合:「只見得一片雪白、粉白、霧白,紛紛落落地營造出一種濛濛的光暈,陽光底下看起來,眼睛都要閃痛了。」再來便是「大象灰」,「這世上竟然有某些顏色是昂貴的⋯⋯大象灰,聽起來不起眼的名字,那灰色若不是使用高級皮革,並且透過特殊的調製鞣製印染,不可能呈現出來,沒有經過複雜的工法,最後只會變成老鼠灰。」陳雪的小說便似那法國最奢靡的皮革名店,凡俗者總被滿櫃的時裝或前頭的金工珠寶所誘,可那以Madame小牛皮、Epsom牛皮精巧鞣制而成的大象灰或班鳩灰,穩當地收在暗架,必得等候暗語、確認眼神,才能成為那識貨人。它才是每個名字後的一生歷練,如玉髓、岩腦與樹之琥珀。這本《親愛的共犯》可被視為影像的衍生空間,另一部獨立於陳雪「空間三部曲」中「大樓」(《摩天大樓》)、「小鎮」(《無父之城》)、「海島」(尚未出版)寫作版圖外的作品。雖然,小說也極大程度的貼著「文明街四十五巷」那座白色大宅的空間伸展枝枒。但陳雪大幅地縮砍獨白與囈語般的文字句式,把枝枒留給顏色、形貌、建築與故事情節,這使得它的文字也變得近似一座建築。透過指令、聽聞線索,讀者便成為了觀眾,小說中長出樓宅、看見人影,影視化的野心由此可見。沒有野心的書寫,難以成就偉大的作品與作家。每當作家一開始寫作,作品就脫離了他自身,從陳雪的寫作段落中,偶爾剝離如降靈般的感受,比如寫夢論夢,醒覺而別緻。小說中能以夢探案的刑警周小詠,這麼說起她的夢:「如今的夢,都像是白天工作的延續。」、「她知道這不是託夢或什麼神奇能力,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她思念父親、努力破案,兩者合一,就成了夢裡辦案的情節,但這就是她想要的。」在這裡,夢不是神諭,夢是野心。小說家和刑警和世人相同,自以為通透如解夢者,皆為夢遊者。正如寫出《他們》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這樣定義作家與夢的關係:「我們也許沉溺於夢境,但絕對不是出於對現實的恐懼或者篾視。我們寫作的原因與做夢如出一轍,我們沒法不做夢。寫作的人是嚴肅的做夢者。」這是一部推理小說,小說理所當然的推向了犯罪者的謎底,卻提供了另一個思考與暗號:「有罪等於可恨嗎?」同時,這也不只是一部推理小說,因為它不斷給予提示,幾近心理暗示。翻開書頁,小說之前,你首先會看到「天空是白的,但雲是黑的。」這是出自經典法國電影《新橋戀人》裡的一段台詞——它更是確認彼此相愛的密語,雖然大多數的愛情,總是危顫、瘋癲與不公平的。愛這件事,果然與小說很像,可能罪惡,卻不一定可恨。本文作者蔣亞妮1987年生,台灣台中人。 摩羯座,狗派女子。無信仰但願意信仰文字。東海大學中文系、中興大學中文所畢, 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中文博士班。 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請登入遊戲》(九歌), 2017年出版《寫你》(印刻), 2020年出版《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悅知)。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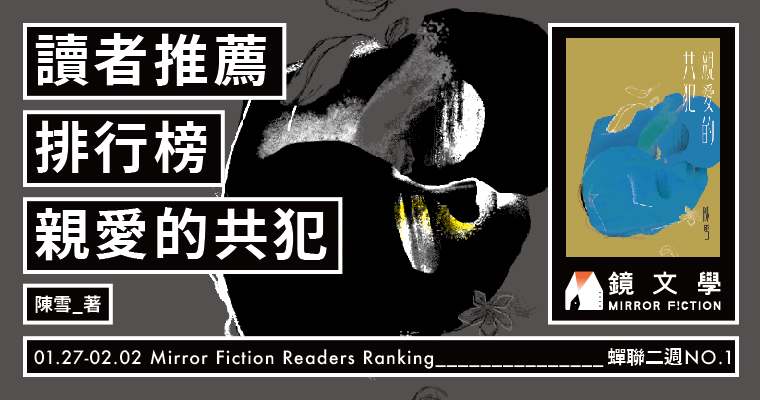
【人氣作品,不看嗎?】讀者推薦排行榜 1/27 - 2/2
鏡文學簽約作品每週【推薦排行榜】♕TOP1 《親愛的共犯》TOP2《無線人生》TOP3《見鬼的法醫事件簿》TOP4《不能讓老師發現的霸凌日記》TOP5《乩童警探:死亡的深度》
+ More
【人氣作品,不看嗎?】讀者推薦排行榜 1/20 - 1/26
鏡文學簽約作品每週【推薦排行榜】♕TOP1 《親愛的共犯》TOP2《貓記憶的21天》TOP3《渡書師:後日》TOP4《台北故事》TOP5《渡書師》
+ More
無以為家的人——專訪陳雪《親愛的共犯》
陳雪一直在浪頭上。從90年代開始,她是弄潮兒也是酷兒,時代迎面而來,便理所當然的用盡生命書寫。我問陳雪,「現在還有人用『酷兒文學』稱呼你嗎?」她回答,「很久沒聽到了,大概很少人知道那是什麼。」2019年陳雪隨同婚法制化結婚成家。看起來,90年代那個披酷兒文學先鋒標誌上陣的陳雪已遠。然而要到新作《親愛的共犯》,我們才發現成家後的她成了潛行者,矗立一座家,悄悄從內引爆。「如果沒有原生家庭,只能自己去尋找家的話,這個可能性是什麼?」陳雪說。這或許可從她在小說前引用的電影《新橋戀人》台詞「天空是白的/但雲是黑的」看出端倪。盲女與流浪漢在廢棄的橋上相遇,不見於社會的愛只能在不是家也非一般人棲身之所的橋上滋長。當愛始自荒蕪,家的意義便同步塌縮。《親愛的共犯》陳雪 著出版日期:2021/1/29亮麗的家埋藏著什麼過去陳雪創作出一個個罷家女孩(藉逃離原生家庭,反省親密關係),現在她一手寫戀愛課散文,一手搭起《摩天大樓》,具象化社會結構與受困其中的人;再來她搭建《無父之城》,搬演終極的暴力——白色恐怖。《親愛的共犯》以一樁富二代綁架案開始,自幼失父的女警「周小詠」進入豪門調查,卻發現侯門似海之外,受害者與加害者的位置也開始混淆不清,最終成為《白夜行》式愛與惡的辯證。我們到最後才明瞭愛是救贖,也是諉過。陳雪在《親愛的共犯》裡搭建一個整潔美滿又安康的家,裡頭的人卻不幸福。再明亮宜人的家對不幸的人來說,也只是有屋頂的天葬。《親愛的共犯》觸及不同階級對家的想像,來自陳雪過去對家的不滿及憧憬,「小時候我很討厭家裡的巧拼跟三層櫃,心想為何大人都買這種東西。後來我認識一對夫妻,他們家充滿廉價家具,毫無美感可言,我卻感到家的感覺。漸漸的,我發現你去很高級的地方,即使像飯店美好,但你不會稱為家。」「現在大家常常談斷捨離,想要乾淨清爽的家,更好的生活,然而裡面的人的狀態是什麼?當我們期望乾淨整齊的美感,就很容易不自覺的高人一等。使用美的東西,其實不會讓人心裡變美,更多時候是為了隔開混亂與骯髒,同時畫地自限。」因此,《親愛的共犯》開篇便是富豪「張大安」蓋的「白樓」。陳雪這樣描述:「一棟白色的建築在夕陽映照中,呈現出幾近金色的光輝,倘若有一雙眼睛從空中俯瞰,將會看到那一棟市區巷弄裡的獨棟樓房,在一片灰色樂高玩具堆起的矮矮樓房中,站立著白色的龐然大物。」▲「我一直想寫育幼院,思考這題材可以放什麼東西。有次在台北市逛街,小小的巷弄有一個工地,正在蓋一個獨棟的樓。不久再去,發現是一個獨棟的豪宅,跟週遭格格不入。我就想:這樣的人為何不去住帝寶?家這個殼會給人帶來什麼?」(圖/鏡文學)在不成家的地方守望陳雪寫家,是顛覆,同時也小心呵護另一種家的可能。《親愛的共犯》另一個重要場景是育幼院。陳雪說她一直對育幼院很感興趣,小時候常覺得自己會被送到那,「因為我父母曾經分開,我始終有種不安全感。那時候《小甜甜》正紅,我跟小甜甜一樣有雀斑,大家就叫我小甜甜。可是卡通裡小甜甜待的孤兒院很溫馨,我的家卻不成家了。」「我對特定空間著迷,總想著這裡面住著怎樣的人?」從《摩天大樓》到《無父之城》,陳雪在封閉的空間中試驗人性。在《親愛的共犯》裡,人物則被放到兩個極端——白樓與育幼院。育幼院培育沒有家的人,那些人長大後會是什麼樣子,會是犯罪者的面貌嗎?答案當然絕非如此簡單。這便碰觸到小說另一個主題——愛與惡的等值。「愛一個人何時會變成惡或罪?」陳雪問道。《親愛的共犯》以綁架案開篇,然而陳雪志不在寫複雜的犯罪,「我不是寫推理,小說裡的殺人都來自人性,而非一個哏,只是想讓人猜不到。」《親愛的共犯》之前,她其實想改寫真實刑案,但發現這些案件原因看起來都很簡單,「可是人是這麼複雜,這些簡單或許有他們無法言說的部分,我想知道人在怎樣的情形下會殺人。」「透過小說,我補足真實案件我看不到的複雜面,更千絲萬縷的看待犯罪,試著找出一個人的生命在何時產生分歧。」因此,《親愛的共犯》看似是偵案故事,到頭來卻展示——陳雪習慣用「展示」描述小說裡的道德困境——令人怵目驚心的悲劇,「我們總以為自己可以改變,活得很小心,往往還是被命運拉了過去。你想擺脫過去的惡,可是掙扎的同時也沾染了惡。」▲《親愛的共犯》延續陳雪前面幾本小說的犯罪題材,不過陳雪說她關注的其實是暴行,以及暴行施加於人後如何與為何不能逃脫。儘管《親愛的共犯》呈現不同的暴行,仍是非常溫柔的小說。或許是陳雪對「家」擁有更多不同想像的自信了吧。(圖/鏡文學)當暴力散發甜膩滋味如何書寫惡,涉及陳雪近年關注的議題——暴行。「這幾年,我一直想寫暴行,施加於人卻無形的暴力,例如控制與剝奪。弔詭的是,這其中有個反覆的模式,傷害之後又呵護。施暴者都有一套說詞,『我是為你好』、『連你都不相信我』等。我想展示這種暴力的形成,以及它如何黏著人。」大至國家機器,小至親密關係。暴力深入脊髓,甚至散發甜膩的滋味,教人錯覺是愛。《親愛的共犯》裡的許多人物正是透過家這個結構,用愛去實行錯。陳雪透露,她曾經歷一段有言語暴力的親密關係,「對方一下貶低自己,一下貶低我,讓我處在是非對錯難分的處境。我一直不願相信自己是受害者,直到對方動手。」「很多時候,愛是只有一個信徒的邪教,對方成為你的教主。」過去陳雪小說常出現青春女孩獻祭的模式——女孩受了傷,用自身的不幸見證社會的殘酷。然而陳雪說,「這一次我的小說人物的愛沒有荒蕪,還有能力並努力去愛。」「不健全的生命,不會去愛。然而我們從小到大會受到各種傷害,因此我們怎樣通過傷害反過來肯定自己,而不是懷著負罪感。」《親愛的共犯》一方面毀家廢婚,一方面展現了最純淨的愛。陳雪寫戀愛課散文,幫助讀者經營親密關係,自認寫散文跟寫小說的人格不同,我好奇兩者差在哪?「寫散文比較接近我自己,寫小說的『我』很淡;寫小說比較能把人放到極端,寫散文是中間值。」不過《親愛的共犯》最後其實帶著異常溫柔的質地。對此,陳雪說或許是自己有了家庭後,對家的想像更有自信。「我發現家未必要在一個房子裡,也可以有照顧與歸屬感。」《親愛的共犯》是橋上的孩子長大了,曾經無以為家的人回頭探望現在無以為家的人。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