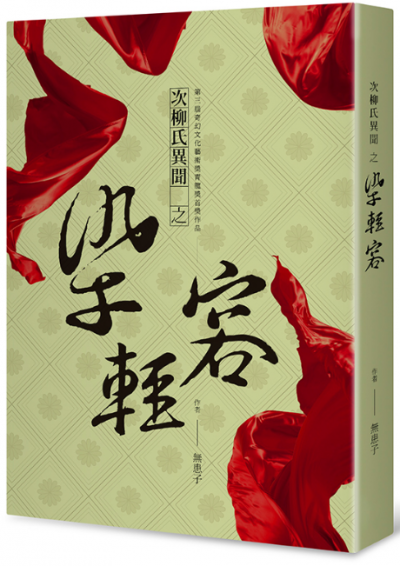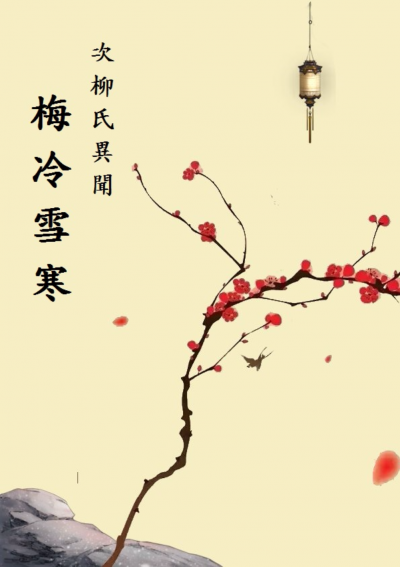馴獸師、雜食閱讀者,近期越讀越發吃力少量,耐性越來越薄,迷戀車上補眠與熬夜,很怕對世界失去興趣。
【深度書評】小部|燦爛如黃花的晚唐,白衣書生的傳奇異聞
文|小部
2019-05-17
在鏡文學見《次柳氏異聞》,頗有他鄉遇故知之感。2009年起,繆思出版經營華文奇幻書系「萬花鏡」,我本本追讀,發現無患子、謝金魚等歷史小說能手(後者如今已是著名歷史普及網站「故事」的創辦元老,其《崩壞國文》更在書店賣得嚇嚇叫)。幾年過去,繆思收場,其作品不是轉移到木馬出版,就是版權回歸作者,世事無常,小說常在。如今重閱舊作,補上當年未出版的篇章,心情卻有些忐忑,到底昔日愛好是真識貨,又或者年少無知的高捧美化?可隨著嘴角的上揚,答案自是揭曉。
無患子的《次柳氏異聞》系列,以晚唐為背景,描寫替人捉刀的白衣書生柳飛卿的種種奇特經歷,以中短篇篇幅,網羅各色類型,時而玄怪,時而淒涼,時而情愛。更特別的是,小說穿插種種唐人生活細瑣,卻能做到細緻而不堆砌資料,長安城區街道勾勒一清二楚,詩文典故信手拈來,〈染輕容〉題材取自《酉陽雜俎》猩猩血記載,〈書中自有〉揉合了兩篇唐人傳奇〈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的架構及精神,〈鬱彼北林〉引司馬遷〈西南夷列傳〉,述說邛都國存在……,更可見作者高才博學,文、史、雜學無一不通。亦諧亦莊的筆法,更令小說兼具可讀逗趣與料峭深沉,氣氛切換自如。
年歲增長後重讀《次柳氏異聞》,更意識到柳飛卿的性情奇特,他有著文人的瀟灑任性,亦若尋常百姓吃瓜看戲,還天生自帶衰運,不是要幫蜘蛛精找單戀情人(蟲緝絲),就是被迫成為高人徒弟,強逼點穴拜師(染輕容),連山林遇狼,請土地公保庇,卻碰到久久從地府陰間返回人間遊賞的劉備與諸葛亮,更開啟了砍殭屍打怪之旅(鬱彼北林)。可別看他總奔波勞碌,就誤以為他就是名搞笑丑角,那是他的好友崔相河的人設,固然屢屢奇遇,令人哭笑不得,柳飛卿實質被寄託更多晚唐士人感懷,〈十八骨傘〉內,他從追查古傘身世,牽引出對老邁教坊樂師的堪憐悲憫。〈縛紅絲〉中,他作為旁觀者,目睹士人為求富貴捨棄癡心舞妓,攀附高門貴女的悲劇,雖是好友兄長,不願評斷,可心底卻更為青樓女子抱不平。
而最能顯其文人抱負的,莫過於〈書中自有〉。崔相河視之珍寶的歷年策論範文,柳飛卿以「東西」輕賤稱呼,還理直氣壯:「我們這身學問,將來也不是貨與帝王家,換幾石米回來填飽肚子罷了,別把自己看得太高了!」這則近七萬字的小說,發展離奇,輾轉描述他跟崔湘河到了霍七家中,後者賤售古籍實屬無奈,乃因遇鬼而被迫脫手,出於好奇,柳崔二人留宿待鬼,卻雙雙捲入奇境。柳飛卿成了玄室國的座上賓,是玄王從大唐天朝迎來的貴客,希冀其智力兵法能救助他們於鄰國蟠木國的虎視眈眈。從平凡士子到救國軍師,柳飛卿擔起沉重包袱,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穿越後大展奇才的興奮熱血來得短暫,更多的是重責大任帶來的壓力,目睹老王衰微,王孫跋扈的惱怒與淒涼。不得不說,瀕死返回人間後,小說著實文風驟變,從亡國悲憤到搞笑唐突,看似情緒截斷,大大煞風景,可反思深意,卻覺得這隱隱指向生死榮華富貴,也不過可痴可笑的禪悟境界。
然而,假如被〈書中自有〉的浩然正氣給唬了,以為柳飛卿真是什麼隱遁民間的淡薄名士,未免也高看了他,他的本行可是做代筆捉刀的,試場上替人當槍手,試場外幫人寫些行卷詩文,呈給主考官留個好印象。這樣有幾分文人傲氣,卻還是得勞碌於經濟營生的凡夫俗子形象,要抓得恰如其分並不容易,更別提柳飛卿多數時候並非立體角色,他在小說的作用,多半是推動故事發展,可無患子仍夾藏不少文人慨嘆,再加上晚唐時局的安排,令其巧思慧黠格外引人矚目。
整系列並未大肆渲染頹敗氣象,無患子筆下的士人依舊苦讀應考,依舊愛湊熱鬧,依舊貧嘴戲謔,依舊上平康坊找煙花女子尋歡。可小說在細微處,仍然可見盛世衰微後的歷史遺緒,比如蜘蛛精谷承塵的一柄寶劍,被人看出乃藩鎮動亂時,節度使豢養的死士遺物;比如依附於梅樹的幽魂,乃三十餘年前甘露之變,清君側不成,暴屍於市的忠臣。而柳飛卿的飛卿二字,取自溫庭筠溫飛卿,溫老前輩同樣是晚唐人士,作為花間詞人,浪漫成性,柳飛卿的人設延續於此,卻不止步於此。無患子不只想寫出一個紀錄晚唐的人,而是一個活著的人,他會遇難,會冒險,會探案,甚至捲入愛情公案,在那些或離奇或淒清或令人嘆惋的傳奇裡,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