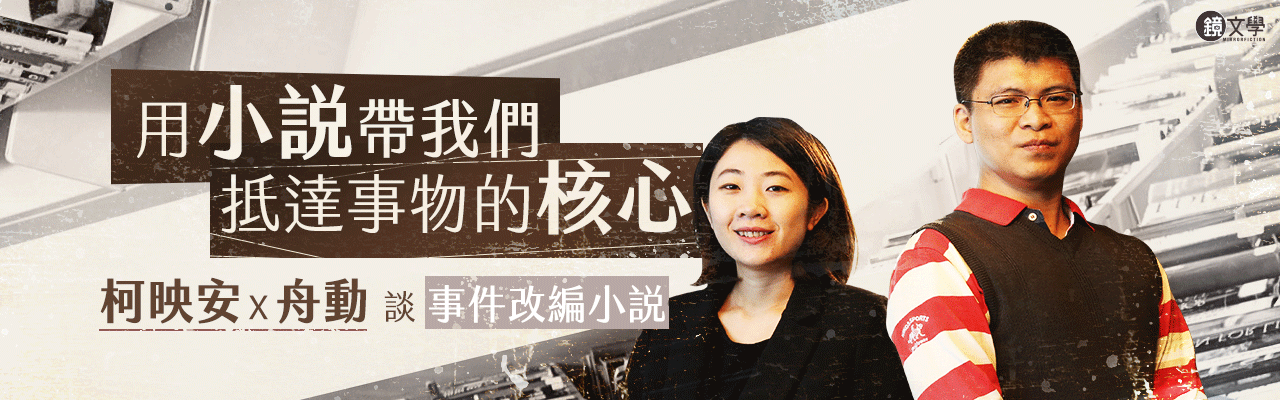【作家特写】用小说带我们抵达事物的核心——柯映安 X 舟动谈事件改编小说
文|翟翱 摄影|赖智扬
2019-01-29
 立即阅读:《无恨意杀人法》
立即阅读:《无恨意杀人法》
鼎鼎大名的佛斯特对小说曾有一个古典而永恒的定义:「它依傍于两座峰峦起伏但并不高峻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一边是历史。」说明小说依附历史之真实,同时唱和诗的抒情与言志。
镜文学即将出版的舟动《无恨意杀人法》与柯映安《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正是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小说。前者以台湾的无差别杀人事件为架构,后者则以田调对象——娱乐女记者——的经历为基底;若以佛斯特的譬喻来说明,《无恨意》或许更依傍历史的山峰,而《女记者》则近于诗的那一端。
尽管如此,两部作品都与现实世界拉扯,或对抗,或对话。因此,两位作者谈创作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运动伤害」,有交集也有同中存异之处。
在既有主题中连结自己好奇的部分
 立即阅读:《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
立即阅读:《死了一个娱乐女记者之后》
一开始,我好奇两人如何选择所写的事件,或者说,该事件之于他们有何可写之处?在写作《无恨意》之前,舟动已出版《慧能的柴刀》、《跛鹤的羽翼》等推理小说。在《无恨意》里,他将社会事件与阴谋论牵连;读到最后,我们才会发现这些看似随机或说无差别的杀人案,背后其实有更大的恶意存在。
「镜文学找上我时,给我很多案件,其中之一正是我很想挑战的。」何以言挑战?舟动表示,「凶手为何如此」是他看待犯罪时最感兴趣的。郑捷事件之后,他开始关注无差别杀人(他习惯用「无差别」而非「随机」这个词),而凶手动机正是这类案件中失落的一环。再者,他自《跛鹤的羽翼》开始将社会议题(家暴)放入推理小说中,因此,想藉由《无恨意》处理看似无以名之的恶。恶是否真无以名之?小说最后,舟动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
柯映安《女记者》以一桩娱乐女记者死于毒趴的耸动事件开头,带出女记者是为钱还是为新闻而死的疑问。正当读者以为这是一部女记者奉献己身、追求新闻的热血之作,小说又一下掉入「荡妇羞辱」的泥淖中;女性在其中动弹不得,包括在她们抛头颅、洒热血的职场上。
柯映安大学念的是历史,此前多写剧本,《女记者》是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最初,她接受镜文学邀请,为的是根据受访者经历,写一本女记者职场故事,「但实际访问后,我发现我需要帮助受访者思考:『外界到底好奇我们什么?』因为她可能觉得娱乐记者是很平常的工作。掌握这个脉络后,我发现女记者不只要面对办公室,还要对付经纪人、艺人,双方互利共生,甚至相互讨厌还得合作。」
至于在这之间让女性无所遁逃的,则是凝视的眼光。
 柯映安与舟动都用事件改编小说来回应他们对台湾现下此刻的观察。
柯映安与舟动都用事件改编小说来回应他们对台湾现下此刻的观察。
「女性在社会观感下,常常因被凝视而做出被迫的反应,但有时这又是很幽微的。例如我在一个男性较多的宴会中,下意识的帮大家倒茶。倒完茶后,我问自己:『为何这样做?』却没有答案。这可能是很多女性会有的习惯,而男性也习惯了接受。女性随时都感觉凝视的眼光,又置于如此复杂的职场,让我觉得可与小说谈的性议题结合。」
性,在此成为权力的展演,也是女性遭受凝视的体现——每次有性爱自拍或影片外泄,在PTT或各大论坛就会有乡民求上车、喊加一。柯映安不讳言,同为女性,那些推文对她而言,已是一种伤害。然而,若与之认真,对方可能会觉得自己只是在开玩笑,「但这如同许多网路上看似玩笑的厌女言论,其实更严重,因为他没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很恐怖。」反过来说,乡民何以觉得可以在中性的网路空间里,肆无忌惮的开女性玩笑?是否预设了网路是男性的场所,女性在此仅是被凝视的客体。
田调资料有了,取舍才是关键
舟动透过《无恨意》探问人性,柯映安则由《女记者》之死检视这个社会。他俩经由小说丢出同一个问题:「台湾,何以至此?」不同的是,舟动著眼于阶级,柯映安则关注性别。小说之于这两人,看似是理所当然的面对社会的方式。然而,两人也经历了相当的田调,才让小说信而可征,尤其是舟动。
「我读了无数的判决书来分析案情,以及各式精神鉴定报告,将律师会遇到的法律问题与精神鉴定如何进行,都融入了小说。写作时,最重要的是时间轴,例如故事要放在一审二审还是最高法院,这些都得厘清流程,再抓出时间点。」舟动说,他写到每天睡觉都还要想事件始末,写完了才能走出来。
同时,他实际走过小说里每一个场景,并将之拍下;写作时,一个视窗开照片,一个开WORD,藉此「感觉那里有一具尸体,有人在逃亡。」这些便是为了「将小说在地化」的一部分。因为舟动认为,「推理小说本身是舶来品,如果只依循欧美那一套,跟外国作品有什么不同?」
不过材料蒐集到了,如何取舍又是一大学问,「例如判决书,你不可能完全放入小说,所以要思考把哪一段放入。还有我用场景描写呈现法医鉴定的凶案现场,也是转化资料的方法。」对舟动而言,很多材料其实「过硬」,却是必须的,他选择将之保留在小说——因为唯有厘清事实,我们才有客观看待案件的可能。
「其实很多资料搜寻就有,但大家不去看,那我就透过小说让大家看。我希望读者踏出同温层,看看不同的东西。」舟动如是作结。
 柯映安比较常读历史科普与人类学书籍,接触较多的叙事文本,反倒是电影。访谈中,她也不经意的引用《一一》里的那句:「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来说明小说之于我们的意义。
柯映安比较常读历史科普与人类学书籍,接触较多的叙事文本,反倒是电影。访谈中,她也不经意的引用《一一》里的那句:「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人生延长了三倍。」来说明小说之于我们的意义。
相较于舟动得与大量文献资料搏斗,柯映安的田调看似简单,受访者的态度也很开放,不过她仍面临困难的取舍,「《女记者》虽是根据真实事件,但故事在写人物,所以我选择的是『我的人物有办法做到,或他们在这个状态下可能做出的行为』,再依据人物内在逻辑与目标来挑选素材。」
「当田调资讯太多,我就必须一再厘清:『主人翁走到这里,她的困境够了吗?足够推动她去做下一件事情吗?』之后再问受访者,便常常获得想不到的答案。」同时,柯映安必须确保田调资料不偏离小说主轴,在天女散花般的资讯中,撷取故事前进该有的样子。
给出观点,是改编的意义所在
小说处理如此现实的题材,如何与之保持距离,又不歪曲,成为改编事件小说的难题。舟动费心的想呈现小说的在地性,其实正是为小说最后给出的惊人谜底铺路;柯映安则紧抓人物内在逻辑为钢骨,藉真实事件为其添加血肉。我由是好奇,真实事件会不会让他们绑手绑脚?
舟动认为,「重点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观察来切入该事件。」他并以普悠玛出轨为例,「一开始我们可能责怪驾驶,后来才看到结构面的问题,这样的事件应该由代议士处理,而小说家也可由庞杂的事件中搓出一条线、一个主轴、一个观点,让人们看到其中的过去与未来。当然,作者不可能呈现全部的观点,他永远都是主观的,只能尽量达到多重观点。」
柯映安则以她自己过去改编的一个新闻事件为例,说明事件与小说间的关系。「有一则新闻是爸爸把老婆打跑了,之后独力扶养两个小孩。有一天,他中了两千万发票,于是忽然从很糟糕的爸爸,变得努力规画人生,重新振作。结果最后他得了癌症。」
就新闻读者而言,这则曲折又带有黑色幽默的事件已说完了,但柯映安的观察是:「这个爸爸在中产阶级眼中,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可是他如此糟糕,或许是因为觉得自己永无翻身的机会。」因此,她想知道「这个爸爸有了希望,会做些什么?他和儿子之间有没有和解?」
「我在意的是小说有没有给出一个观点。」柯映安说。这也唱和舟动认为作者能理出一条线,藉此映照事件的说法。
离开同温层,但读者都在同温层
访问最后,我好奇他俩从写之前到之后,对议题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舟动说,「一开始只知道受害者,读了判决书才认识加害者。」因此,更不要说那些只看新闻了解案情的人——乡民的正义可能不是正义。柯映安则藉写《女记者》确认了她对女性处境的观察。至于多理解的,是记者生态。
 舟动是英语教学者,写推理小说之余,也评推理小说。在他身上,可以看见创作者对作品的要求与自我砥砺。
舟动是英语教学者,写推理小说之余,也评推理小说。在他身上,可以看见创作者对作品的要求与自我砥砺。
「其实记者是很孤独的,他们很少收到回馈。新闻写得很好,但主管不会称赞你,阅听人更不会,因而陷入『我用什么东西证明自己』的纠结。小说里,主角跟配角辩证新闻在他们心中究竟是什么?这背后要说的,其实是如果记者把新闻当作自己的作品,会过得很痛苦。」
呈现社会舆论或说乡民反应,是处理新闻事件小说不可避免的环节,《无恨意》与《女记者》也不例外。在此,他们既是作者也是小说的一部分,因为在网路中,他们与读者——广大的乡民——无异。然而,柯映安坦言她已渐渐避开那些看了会受伤的留言,「或许这代表退缩到同温层了吧。」
访谈过程中,我们一再提到同温层,也希望众人离开各自的同温层。这显然并非易事。小说,作为提供异质观点的手段,当下的处境或许更为艰困。处理跟主流意见相左的小说,就像在逆风处写作,有著不小的运动伤害。
写作是孤独的,更孤独的是小说家想藉此呈现他心中本该是如此的世界;正因他们不认同这个版本的世界,所以创造了一个更良善的。因此,广袤之中注定了一开始只有小说家踽踽独行。我想起舟动说的,「写作初衷是好的,那就去做吧。」
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理由不做。
因此,小说家会继续在事物的核心处,所有线索指向真相之地,等待读者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