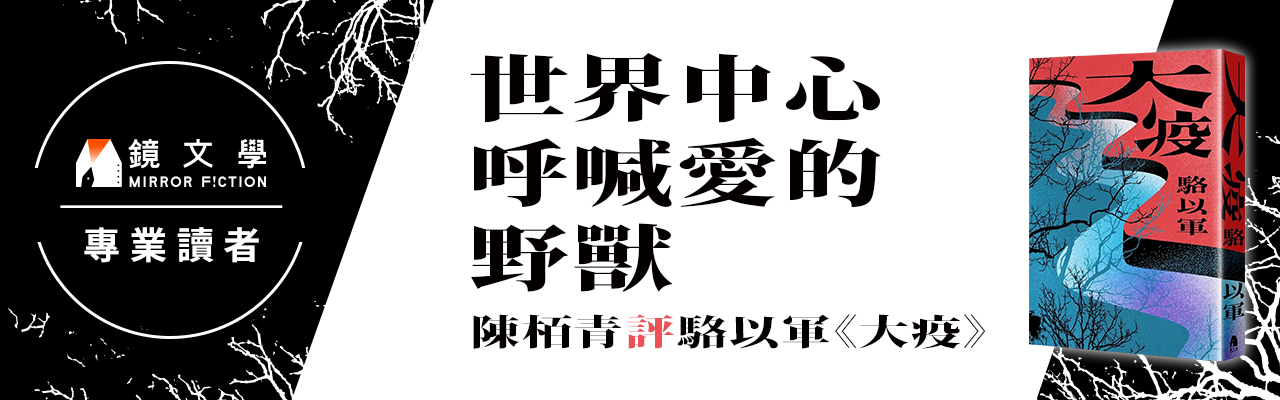世界中心呼喊愛的野獸——陳栢青讀駱以軍《大疫》
文|鏡文學
2022-10-13
駱以軍小說《大疫》中有兩個明顯的敘事指向,一端動輒拉升到「全人類」、「代」,族裔或種之興亡感嘆,至大至高。一端是極小極細,對「當代生活」、「個人感覺」的深掘與命名,素描了個體心靈震顫一瞬。讀《大疫》時不有刺激感,在於心念電轉間,見小說家筆尖作大怒神甩,轉瞬可由全人類的尺度、文明的興衰起滅瞬移至生活中忽微「心內彈琵琶」、頸後細毛皆為之縠餗顫慄因為他描述而有共感的日常度量橫。
這是駱以軍小說中隱在的張力,或曰之戲劇感的由來。

駱以軍 著
出版日期:2022/8/5
但我是想問,在那中間呢?在這極端的兩造,在「全人類」尺度和個人微感覺之間,那本來就什麼都沒有嗎?有什麼作為緩衝、鋪墊、漸層色或轉場?或者,有一個什麼是聯繫並策動這小大與輕重之對比,實乃是小說家真正欲言的?
借《大疫》中小說家自語可能是,「這是個什麼都沒了的小說」。
但分明那麼美那麼美,怎麼會「什麼都沒了呢?」,駱以軍『大疫』裡頭,琉璃珠串那樣成串成撥,靈動的比喻,小丑魚一撥尾巴,無數海葵觸鬚刷刷變顏色換臉的長短句法,讀《大疫》本身確實像一種熱疾,一種上癮。
但又髒掉了。從「事件」之後,讀駱以軍變得艱難。從此以後,你看駱以軍,他寫大疫,寫疾病,你橫著數著看,你覺得那說得不只是疾病,不只是一場改變人類的大疫。
就老實說吧,所有讀《大疫》的人,都想知道,他是不是倖存了?他的傷害平復了嗎?他被毀掉了嗎?他會用這本書回應一切嗎?讀者總在找上文那個「中間的什麼」、「真正想說的」
恰如《大疫》中作為對話的潛文本之一的《紅樓夢》,榮寧二府興衰是由甄士隱和賈語村引出,故事到底是「真事隱」、「假語存」,恐怕,這只是我設想,《大疫》中驅動書寫衝動的關懷面相或說核心已被先天的(不直接說,藏在小說其他敘事裡),或者後天(變成書的過程中直接刪除了。),形成一個巨大的空缺,小說家的原始敘事衝動,興或我們已經不可而知了。
可有一個聲音是實實在在,刪不掉的,作為一段病毒的螺旋碼,也是《大疫》的內在基因序列,每隔幾章你無法不聽到一段旋律,他反覆,他不停浮現,如這一段:
他說:「我找了許多可以轉譯成基因序的人類語言,譬如披頭四的歌,譬如春江花月夜….但那些單股DNA,在寄主細胞內的反轉錄,箝上,既使控制了宿主細胞,但那個圖片的週期太短了,幾乎可以說兩三天就成為亂碼…..你知道最後成功的曲子是什麼嗎?」
他用粵語鄺美雲版的柔美唱腔,輕輕唱著:「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我的眼淚忽然一直流一直流。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
那是心經。小說中心經繕寫了何止一遍。
這便成大疫的奇觀。一方面,小說家的筆無物不可寫,無事不可說,時作雄辯滔滔,時有柔情哀婉,寫什麼都明白曉暢,說什麼都美不可方物,「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他心通,天眼通,說到口乾舌噪,說到來日大難。他甚至能召喚人類的文明全景啊,他能寫你個人纖毛那樣微細的感覺。
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連這樣文字都無法,或不能去述說,只能歸結到心經中,「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在那樣意義被無窮盡懸置的音節性咒語裡被安放。
讀者只能不時聽到小說中說故事的人嘆息:「太苦了太苦了。」
但到底痛苦的核心是什麼?填充在全人類和個體,在至大之群和至小的個人感覺,在歷史與當代之間,我卻們只聽到心經迴盪。
小說中角色所言不免讓人多做聯想:「太苦了,真的太苦了,怎麼能輕盈靈性,願意原諒,好聲好氣的說『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如何還願意坐下來,那麼柔慈的說:「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詞。」?」
心經、真言由原始語文翻譯成中文而剩下字音,字面上毫無意義,卻也蘊含一切意義。虛空藏,他只能被壓縮,卻無法還原。
《大疫》是故事會,是大夥湊在一起說故事。但所有人的故事,聽起來都是同一個聲音,那就是痛苦。他可以被壓縮,但無法解壓縮。你看到至大(以人類為單位元的)與至小(個人的發散),卻無從知道連結。他充滿碎片,但本體和必然大於原始。彷彿什麼都說了,但到底「什麼都沒有了。」這一個疫的奇觀。關於痛苦的本質性展演。通透,卻透明。可以言明,不能明說。
群體的瘟疫
《大疫》中明面以現實疫病為時間線索,半真半假敷演一個人類滅亡之世。但在小說裡還有一個斷代可作為「疫」降臨的時間軸。
我們可以注意到世代的體現。《大疫》中有諸多對世代的思考:「我們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唯一經歷過,感覺的塞滿,過剩到不可思議的地步,然後忽然間什麼都沒有了,唯一有這樣經歷的幾個人」、「 因為網路的發明,人們後來活在一個,每天為單位,數百倍於古人的經驗的,萬花筒、繁殖簇放,所有情境訊息全爆炸,兜覽進『你』這個感受者的大腦」,亦即,網路之高度覆蓋作為世代的斷代點,駱以軍要說的是資訊爆炸、時間感知比以往更快速,人們的思維、群聚方式、人際關係都因此產生改變。
小說家因此也對網路世代的孩子做出側寫,「這些年輕人自主運動的液態群體移動,可以形成全新的大故事,但同時似乎在自己只是其中一個小光點,」「全部單子位但又聚集成一大群。」
與此對比,小說中還有一些人「是網路世代之前的」、「一個比較寬鬆、渺小個人或被剝削,但不至於全部腦力和激情,全上繳一個雲端」、「比較廢」的世代。小說家自己是屬於這代的。
所以,世代的差異是存在的嗎?這無法否認。但我不覺得駱以軍頻繁提起世代──年輕VS老。老頭子VS網路新世代──做的是操作世代對立,事實是,一個理想之境應該是《大疫》中所引用的赫爾曼.布洛赫之〈夢遊人〉片段:「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屬於不同世紀的人,可他們卻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甚至是同時代人,這或許可以解釋他們為何那麼不穩定,難以合理地理解彼此,異乎尋常的是,儘管如此,還是存在著一種人與人的團結一致,一種橫跨歲月的理解。」
一種團結與相守。跨越世代之間彼此的傳承,互相扶持。那不也是小說家透過山谷中彼此接力說故事體現出來的人類劫餘之境?
但這樣一個人類科技與文明興盛終於能「讓自己舒服」的伊甸園、科技天堂,也帶來陰影。那是什麼?那就是網路罷凌的出現。或說者,罷凌背後要講的是,「群之暴力」如何在網路媒介上體現:
「『龐大數量的人群,突然變異成蝗群,單一反應模式』,但其實搞不清楚自己只是躲在龐大的群體裡,猥褻的窺淫者。這種集團性理直壯。」
「下個標題,人們就全瘋了撲向那『最壞最邪惡的滲透者」、『妖怪』、『病源』」
那是《大疫》中「病毒」的另一個象徵所在。小說家設想,「這次的大瘟疫或許也正是我們人類這三十年附著在其上,建立起來的網路新世界。超快速流動的龐大人數、金流、欲望、故事、短敘事,好像本就在搭建一個讓人類自我簡化,以合乎傳輸規格的龐大風月寶鑑的鏡像投影。」
說起來網路環境所能趨致的暴力和人類世構成的瘟疫何其相像。
而小說中說故事的人是誰呢?無論是說故事的是他,或是她,那人總是那被「群」所傷害者。
「她如果內在有一天平的秤坨,那就是『人不該無意義的羞辱他人』。
「她的感想是,人非常軟弱,比一般想像的要恐懼群體的霸凌 」
群體為何可以變成暴力?小說家在《大疫》中追溯了台灣歷史,中國近代史中的群之暴力。族群如何被化約成群,早年台灣開發之械鬥、中國文革的暴力,而在此刻讓小說中人可感的是網路上,「新網絡、 新故事具有極大的排他性。 」
張愛玲「惘惘的威脅」在《大疫》中成了「網網」的威脅。但何不將這解讀成,對於群之暴力的疲倦和厭斥。
那是在自杜斯妥也夫斯《地下室手記》的遙遠回音,「我是一個,他們是全部。」 小說家體現的地下室是,群,或是代,他們是一群,是一代,但我是一個。
我是之外。
我是那多出來的。
小說裡的山谷容納文明剩下來的人。
小說中人則發現山谷中不停冒出「多出來的人」
與其說增生,多出來,但何嘗不是,零餘。
從這裡我也很不敬的想問,你大爺駱以軍真的關心現實中瘟疫這個問題嗎?
在我看來,「山谷外大家都死了」和「大家都活著」其實是同一個意思。
瘟疫之外,一種暴力早殺死人無數次。群的暴力。網路暴力。
而他是群之外的人。
被傷害者。被孤立者。
我輩孤雛。
之外
之外在此有三個維度。
一者,事關大疫的寫作策略,和書寫者對小說、故事的認識。
所以,成為小說家意味著什麼?
那麼古典的,我們又回到愛倫‧坡小說《在人群中的人》,或班雅明論波特萊爾,「在人群之中,卻又像在人群之外」。在《大疫》中,小說家使用了科學性的「觀測者」這個詞彙,「「這些變態、異化,或說小小的變態,當事人自己都不知道,有一個和他們一樣隱匿於撩亂人群中的觀測者,其實已盯上了他們。」、「那些不會知道自己可能只是因生存、夾混在那偷拐搶騙、吹奏彈唱的形貌、嘴臉,被一旁一個觀測者記錄下來」
照他的說法,小說就是「第二次」、「如那個女作家寫的:『滾燙冒煙的熱水沖進白瓷壺裡,那些枯萎乾燥的菊花又一朵朵重新綻放,第二次活過來。』」,而「『第二次』才能體會『結構之所在』」
小說家這些論述,這一方面說明故事的權柄,透過說故事,經驗得以被流傳,情感被傳遞,人類證明自己活著,「你又再活了一次。」
一方面也側面說明了小說的契約--「在閱讀小說時,我們有一個默契,那是一個『風月寶鑑』,鏡中倒影.......他們都只是『戲』、『故事』搖晃擺弄的傀儡。現代小說的出版,被書店、出版社、購買者、學院交叉 確認那是『一本小說』,而非社會版新聞或狗仔偷拍。」
小說不是新聞,不是八卦,不是紀實,不能照單全收……
《大疫》回到「一群人在山谷中說故事」這樣簡單的,古典的構想上,小說家展示了各種說故事的奇技淫巧,駱以軍是說故事的人,我以為他更側重在「說」之上。說起來,不滿足於故事,那不就是「小說」的誕生嗎?
小說不只是故事。
《大疫》是駱以軍技術的的奇觀,述說痛苦由來的核心被鑿空(或打散),但技術的硬核面,撐持一切的小說術鋼筋卻裸露了。我們可以看到更多他小說觀的建立、對小說的理解和關懷所在。「坦白從寬」,卻在那樣狹窄逼仄的山谷,和險峻環境下(小說與現實中都是),我們看到「(駱以軍)文明的大樓是怎麼蓋起來(或留下來)」
《大疫》作為故事的容器,也是留刑地,這個山谷不只是病毒的培養皿,也是故事在養蠱,穿插各種體例,錯亂時態,顛倒夢想,那就是駱以軍的拿手好戲。也就是《妻夢狗》以來,「時間之屋」的策略。在時間之屋中,不同時段、生命狀態的人被壓縮在一起,擠在同一個屋簷下,小說的行進就是時光之屋中房間的漫遊,而故事到了最後,故事彼此破窗,破格,在某個不可能接口連接上。
「這個小說中的人物,像破碎的漂流物,或不同人之間的夢境之序,竟然可以穿透框架,跑到別人的回憶裡」
「從一個二維世界掙脫冒出…..然後又竄進另一幅畫中」
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橋段,被收容山谷的小說家說起自己的故事,是關於香港女孩安。在安的丈夫過世後,小說家照顧他,對安說故事。乃至安有一天跟他說,自己夢見亡夫了:「他就在一片綠光充盈的山谷中」。小說家忽然有此一念,「我們之所以在此相聚.....全是她那良善的念頭,一順之光幻造出來的這綠光盈滿的山谷」
這是一個故事的迴圈,連還套,站在「之外」說故事的小說家發現,他在對方身上植入一個念,而這個念催動了夢,自己竟可能是被裝在這個過了兩手製造出來的夢/故事「之內」,最外與最內此時成了莫比斯環相連,那在現實中不可能,卻在小說中成為奇觀。
這說故事的策略該也涉及他的關懷。
小說家之書寫一直有一種敏銳,他筆下總寫日常的傷害不停發生,「但只有我知道」。那意味的是,秘密的誕生。從此,我跟人不一樣了。秘密帶來的是(說故事的)權力,卻也伴隨痛苦。是詛咒。無人知曉。
這似乎也是駱以軍從出登場文壇後問出的著名問題———最裡面的房間到底有什麼?
《降生十二星座》告訴我們,最裡面的房間並不在正中央。而在於封閉性。那是無法進去的,直子之心。
而小說家則在小說中製造不可能的奇觀,奇蹟,試圖尋找、破譯那個秘密──進入最裡面的房間。而進入終究是不能的吧。可在那歪歪倒倒的終究徒勞的途徑之中,我們看到的是,你那麼努力了啊,那就是愛之誕生。慈悲之誕生。悲憫之誕生。人性之誕生。
「之外」的第二個層面,從(小說)「之外」來言,也就是和現實的關係,《大疫》中不無指涉的多次指出,「我想許多他的讀者,也會習慣性的把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混淆了他小說中那些怪異變態的思想模型」、「慣性把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混淆他小說中那些怪異變態的思想模型,替他多打開一個超乎正常邏輯之外的抽屜」,我傾向把這視為一個辯解,《大疫》外的小說家也正經歷大疫,不,小說該一直就是他的疫,早在更早之前,人們就不停的比附,查核,檢查他的作為,核實他的政治傾向和思想,確認現實與小說的重合否,那和他的小說術有關,但作為小說家,他本來該在小說這個裝置「之外」,卻因此被捲入小說之中。甚至,小說裡的他可能比小說外還讓人感到存在強烈,小說外的駱以軍變得無比影薄,「之外」被「之內」捲入了,現實和小說破開一個口,他的現實被自己的虛構覆寫,只要他寫作和閱讀的行為存在,這個黑洞就不會消失。
我不知道是小說摹寫了現實,還是現實模仿了小說。我以為那才是奇觀。
綜合上述兩個層面,「之外」延伸出第三個層次,那弔詭顯示,當我們說「之外」的時候,其實已經不是在小說「之外」。
《大疫》中透過小說中人提到:「小姐說二先生說 『我絕不會和他們一樣』,但後來二先生又說『我終於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了。』」
當然這句話可以完全在小說文本層面解讀。但如果對照上述的「之外」層次之二,「事件」的影響效力如此強力,雖然小說中直面真實世界的「事件」本身空缺了,但是不是正因為小說「之外」的強效,他的催哭/摧枯拉朽,才更鞏固上述小說家堅信敘事倫理和小說家位置作為一種「之外」,所以在《大疫》中我們看到故事群、故事聚落、故事的核爆,「並不是疫情來了,我們只好說故事」,而恰恰是「疫情來了,我們因此必須更說故事」,故事本身作為一種隱在的抗衡,上述「之外」的小說倫理作為書寫者自身奉行的第一道德圭臬。它的力量,一種道的理念反而更堅定了。
但另一方面而言,小說家又擔心,面對「事件」,他是不是終究變成「我終於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了」,我也壞掉了嗎?面對暴力,金剛怒目?便又回到那句老話,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
愛的瘟疫
據說《大疫》在前期書名是《愛在瘟疫蔓延時》,成書之時,「愛」不見了。但「愛」又沒有不見,小說家在《大疫》中喜言愛。
小說裡,這個自稱「北北」,這個被社交媒體和政治正確所規訓,必須在小說中不停自承自己是「異性戀直男癌」、「充滿男性荷爾蒙之意淫」的小說家,沒羞沒譟的提起愛。但駱以軍又豈會不知道,從十九世紀以來,愛已經被資本主義,被戲劇被電影被小說被各種雞湯文乃致你我的臉書,消磨的差不多了。
愛本身甚至比他貫穿全本小說的心經,更像咒語,更像是迷面。只剩下字面的意思,像是心經一般。
終究,「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被耗盡了。連小說中人物都跳出來說「愛也被屬於他的抽象維度之病毒感染」,「愛」被他一直說,卻越說越稀薄。
《大疫》中這一頁在談愛,翻過一面小說家就搞起了未亡人你看,又來了。想必所有讀者都這樣拍額頭),「他想愛她」、「但在某種意義上,是他強暴了她」,在他筆下,性是近乎理解所以身心靈交融,卻又無比暴力。小說中男性小說家與安的身體推拒還迎之舞以各種變型散落在《大疫》各事件中,也進出小說家畢生小說中,他總刻意跨過那條線,在倫常、理性、人我關係、社會性眼光之間反覆跳躍,辯證,不停自憐又自恨、自問。俠以武犯禁,駱以小說犯禁,犯罪,更犯賤。
小說家在《大疫》中舉夏目,舉川端,舉井上靖舉三島、納博柯夫等作品為例,那是他年少膜拜的小說,在這些前輩過激作品中(燒了金閣、強暴、堅硬鞋尖踢像肚腹),小說家自承那令他目眩想抵達的是「那非關色境,而是一種『對美瘋魔, 推到極致,停在那火柴棒之火苗將熄未熄之瞬』」
正因為愛被耗盡了──這場大疫也是愛被感染的瘟疫──小說家必須用燒紅的鐵鉗,用磨利的刀尖,或是溼漉漉的臭雞雞。他耍寶,他不惜作賤自己,他毀三觀,「不可以色色」,他搞變態,既「過激」、「超常」,甚至要去「上未亡人」、「像強暴」、「我丈夫死了,從此我就是人盡可夫的女人」,但在這些情節的展示中,無法預測,不能預料,卻又言之成理,在發動的瞬間,包括但不限於,等於更超出,他試圖以此重新電極,或發明「愛」這個詞彙。
說起來,政治正確一定輕鬆多了,或僅僅把「愛」字照本宣科念出來。「可那不是我的忍道。」
就算經歷那麼多,無比痛苦。窮聲哀號。就算被人視為野獸。
小說家悶頭就是要幹,要去幹,他總想用小說體現『停在那火柴棒之火苗將熄未熄之瞬』」。
小說家就是世界中心呼喊愛的野獸吧。
電影《老男孩》裡說:「就算我是野獸,野獸也有活下去的權利。」
而駱以軍再一次用小說趨近「火苗將熄未熄之瞬」,縱然從什麼時候開始,現實之肉身已經成了火柴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