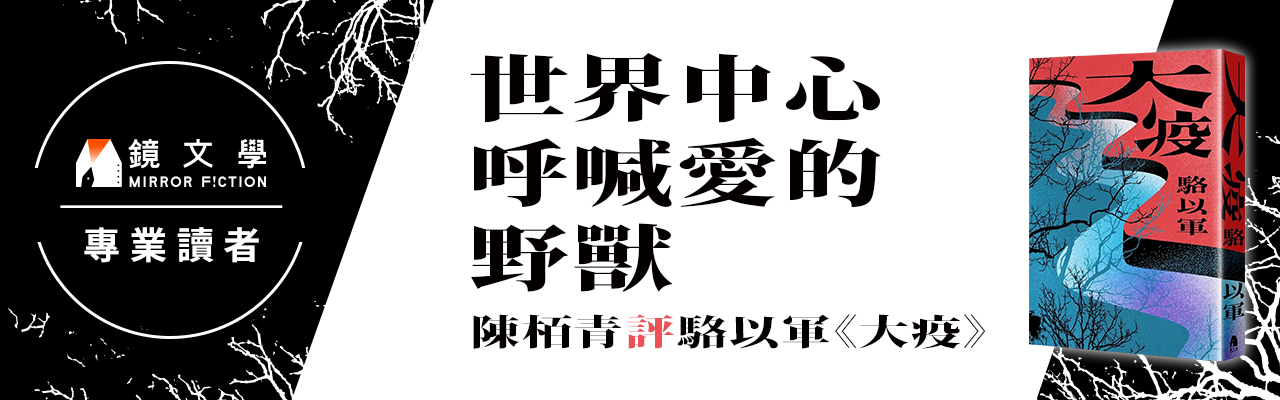世界中心呼喊爱的野兽——陈柏青读骆以军《大疫》
文|镜文学
2022-10-13
骆以军小说《大疫》中有两个明显的叙事指向,一端动辄拉升到“全人类”、“代”,族裔或种之兴亡感叹,至大至高。一端是极小极细,对“当代生活”、“个人感觉”的深掘与命名,素描了个体心灵震颤一瞬。读《大疫》时不有刺激感,在于心念电转间,见小说家笔尖作大怒神甩,转瞬可由全人类的尺度、文明的兴衰起灭瞬移至生活中忽微“心内弹琵琶”、颈后细毛皆为之縠𫗧颤栗因为他描述而有共感的日常度量横。
这是骆以军小说中隐在的张力,或曰之戏剧感的由来。

骆以军 著
出版日期:2022/8/5
但我是想问,在那中间呢?在这极端的两造,在“全人类”尺度和个人微感觉之间,那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吗?有什么作为缓冲、铺垫、渐层色或转场?或者,有一个什么是联系并策动这小大与轻重之对比,实乃是小说家真正欲言的?
借《大疫》中小说家自语可能是,“这是个什么都没了的小说”。
但分明那么美那么美,怎么会“什么都没了呢?”,骆以军‘大疫’里头,琉璃珠串那样成串成拨,灵动的比喻,小丑鱼一拨尾巴,无数海葵触须刷刷变颜色换脸的长短句法,读《大疫》本身确实像一种热疾,一种上瘾。
但又脏掉了。从“事件”之后,读骆以军变得艰难。从此以后,你看骆以军,他写大疫,写疾病,你横著数著看,你觉得那说得不只是疾病,不只是一场改变人类的大疫。
就老实说吧,所有读《大疫》的人,都想知道,他是不是幸存了?他的伤害平复了吗?他被毁掉了吗?他会用这本书回应一切吗?读者总在找上文那个“中间的什么”、“真正想说的”
恰如《大疫》中作为对话的潜文本之一的《红楼梦》,荣宁二府兴衰是由甄士隐和贾语村引出,故事到底是“真事隐”、“假语存”,恐怕,这只是我设想,《大疫》中驱动书写冲动的关怀面相或说核心已被先天的(不直接说,藏在小说其他叙事里),或者后天(变成书的过程中直接删除了。),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缺,小说家的原始叙事冲动,兴或我们已经不可而知了。
可有一个声音是实实在在,删不掉的,作为一段病毒的螺旋码,也是《大疫》的内在基因序列,每隔几章你无法不听到一段旋律,他反复,他不停浮现,如这一段:
他说:“我找了许多可以转译成基因序的人类语言,譬如披头四的歌,譬如春江花月夜….但那些单股DNA,在寄主细胞内的反转录,箝上,既使控制了宿主细胞,但那个图片的周期太短了,几乎可以说两三天就成为乱码…..你知道最后成功的曲子是什么吗?”
他用粤语邝美云版的柔美唱腔,轻轻唱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我的眼泪忽然一直流一直流。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
那是心经。小说中心经缮写了何止一遍。
这便成大疫的奇观。一方面,小说家的笔无物不可写,无事不可说,时作雄辩滔滔,时有柔情哀婉,写什么都明白晓畅,说什么都美不可方物,“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他心通,天眼通,说到口干舌噪,说到来日大难。他甚至能召唤人类的文明全景啊,他能写你个人纤毛那样微细的感觉。
但另一方面,有些事情连这样文字都无法,或不能去述说,只能归结到心经中,“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在那样意义被无穷尽悬置的音节性咒语里被安放。
读者只能不时听到小说中说故事的人叹息:“太苦了太苦了。”
但到底痛苦的核心是什么?填充在全人类和个体,在至大之群和至小的个人感觉,在历史与当代之间,我却们只听到心经回荡。
小说中角色所言不免让人多做联想:“太苦了,真的太苦了,怎么能轻盈灵性,愿意原谅,好声好气的说‘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何还愿意坐下来,那么柔慈的说:“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词。”?”
心经、真言由原始语文翻译成中文而剩下字音,字面上毫无意义,却也蕴含一切意义。虚空藏,他只能被压缩,却无法还原。
《大疫》是故事会,是大伙凑在一起说故事。但所有人的故事,听起来都是同一个声音,那就是痛苦。他可以被压缩,但无法解压缩。你看到至大(以人类为单位元的)与至小(个人的发散),却无从知道连结。他充满碎片,但本体和必然大于原始。仿佛什么都说了,但到底“什么都没有了。”这一个疫的奇观。关于痛苦的本质性展演。通透,却透明。可以言明,不能明说。
群体的瘟疫
《大疫》中明面以现实疫病为时间线索,半真半假敷演一个人类灭亡之世。但在小说里还有一个断代可作为“疫”降临的时间轴。
我们可以注意到世代的体现。《大疫》中有诸多对世代的思考:“我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经历过,感觉的塞满,过剩到不可思议的地步,然后忽然间什么都没有了,唯一有这样经历的几个人”、“ 因为网路的发明,人们后来活在一个,每天为单位,数百倍于古人的经验的,万花筒、繁殖簇放,所有情境讯息全爆炸,兜览进‘你’这个感受者的大脑”,亦即,网路之高度覆盖作为世代的断代点,骆以军要说的是资讯爆炸、时间感知比以往更快速,人们的思维、群聚方式、人际关系都因此产生改变。
小说家因此也对网路世代的孩子做出侧写,“这些年轻人自主运动的液态群体移动,可以形成全新的大故事,但同时似乎在自己只是其中一个小光点,”“全部单子位但又聚集成一大群。”
与此对比,小说中还有一些人“是网路世代之前的”、“一个比较宽松、渺小个人或被剥削,但不至于全部脑力和激情,全上缴一个云端”、“比较废”的世代。小说家自己是属于这代的。
所以,世代的差异是存在的吗?这无法否认。但我不觉得骆以军频繁提起世代──年轻VS老。老头子VS网路新世代──做的是操作世代对立,事实是,一个理想之境应该是《大疫》中所引用的赫尔曼.布洛赫之〈梦游人〉片段:“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属于不同世纪的人,可他们却不得不生活在一起,甚至是同时代人,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为何那么不稳定,难以合理地理解彼此,异乎寻常的是,尽管如此,还是存在著一种人与人的团结一致,一种横跨岁月的理解。”
一种团结与相守。跨越世代之间彼此的传承,互相扶持。那不也是小说家透过山谷中彼此接力说故事体现出来的人类劫馀之境?
但这样一个人类科技与文明兴盛终于能“让自己舒服”的伊甸园、科技天堂,也带来阴影。那是什么?那就是网路罢凌的出现。或说者,罢凌背后要讲的是,“群之暴力”如何在网路媒介上体现:
“‘庞大数量的人群,突然变异成蝗群,单一反应模式’,但其实搞不清楚自己只是躲在庞大的群体里,猥亵的窥淫者。这种集团性理直壮。”
“下个标题,人们就全疯了扑向那‘最坏最邪恶的渗透者”、‘妖怪’、‘病源’”
那是《大疫》中“病毒”的另一个象征所在。小说家设想,“这次的大瘟疫或许也正是我们人类这三十年附著在其上,建立起来的网路新世界。超快速流动的庞大人数、金流、欲望、故事、短叙事,好像本就在搭建一个让人类自我简化,以合乎传输规格的庞大风月宝鉴的镜像投影。”
说起来网路环境所能趋致的暴力和人类世构成的瘟疫何其相像。
而小说中说故事的人是谁呢?无论是说故事的是他,或是她,那人总是那被“群”所伤害者。
“她如果内在有一天平的秤坨,那就是‘人不该无意义的羞辱他人’。
“她的感想是,人非常软弱,比一般想像的要恐惧群体的霸凌 ”
群体为何可以变成暴力?小说家在《大疫》中追溯了台湾历史,中国近代史中的群之暴力。族群如何被化约成群,早年台湾开发之械斗、中国文革的暴力,而在此刻让小说中人可感的是网路上,“新网络、 新故事具有极大的排他性。 ”
张爱玲“惘惘的威胁”在《大疫》中成了“网网”的威胁。但何不将这解读成,对于群之暴力的疲倦和厌斥。
那是在自杜斯妥也夫斯《地下室手记》的遥远回音,“我是一个,他们是全部。” 小说家体现的地下室是,群,或是代,他们是一群,是一代,但我是一个。
我是之外。
我是那多出来的。
小说里的山谷容纳文明剩下来的人。
小说中人则发现山谷中不停冒出“多出来的人”
与其说增生,多出来,但何尝不是,零馀。
从这里我也很不敬的想问,你大爷骆以军真的关心现实中瘟疫这个问题吗?
在我看来,“山谷外大家都死了”和“大家都活著”其实是同一个意思。
瘟疫之外,一种暴力早杀死人无数次。群的暴力。网路暴力。
而他是群之外的人。
被伤害者。被孤立者。
我辈孤雏。
之外
之外在此有三个维度。
一者,事关大疫的写作策略,和书写者对小说、故事的认识。
所以,成为小说家意味著什么?
那么古典的,我们又回到爱伦‧坡小说《在人群中的人》,或班雅明论波特莱尔,“在人群之中,却又像在人群之外”。在《大疫》中,小说家使用了科学性的“观测者”这个词汇,““这些变态、异化,或说小小的变态,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有一个和他们一样隐匿于撩乱人群中的观测者,其实已盯上了他们。”、“那些不会知道自己可能只是因生存、夹混在那偷拐抢骗、吹奏弹唱的形貌、嘴脸,被一旁一个观测者记录下来”
照他的说法,小说就是“第二次”、“如那个女作家写的:‘滚烫冒烟的热水冲进白瓷壶里,那些枯萎干燥的菊花又一朵朵重新绽放,第二次活过来。’”,而“‘第二次’才能体会‘结构之所在’”
小说家这些论述,这一方面说明故事的权柄,透过说故事,经验得以被流传,情感被传递,人类证明自己活著,“你又再活了一次。”
一方面也侧面说明了小说的契约--“在阅读小说时,我们有一个默契,那是一个‘风月宝鉴’,镜中倒影.......他们都只是‘戏’、‘故事’摇晃摆弄的傀儡。现代小说的出版,被书店、出版社、购买者、学院交叉 确认那是‘一本小说’,而非社会版新闻或狗仔偷拍。”
小说不是新闻,不是八卦,不是纪实,不能照单全收……
《大疫》回到“一群人在山谷中说故事”这样简单的,古典的构想上,小说家展示了各种说故事的奇技淫巧,骆以军是说故事的人,我以为他更侧重在“说”之上。说起来,不满足于故事,那不就是“小说”的诞生吗?
小说不只是故事。
《大疫》是骆以军技术的的奇观,述说痛苦由来的核心被凿空(或打散),但技术的硬核面,撑持一切的小说术钢筋却裸露了。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他小说观的建立、对小说的理解和关怀所在。“坦白从宽”,却在那样狭窄逼仄的山谷,和险峻环境下(小说与现实中都是),我们看到“(骆以军)文明的大楼是怎么盖起来(或留下来)”
《大疫》作为故事的容器,也是留刑地,这个山谷不只是病毒的培养皿,也是故事在养蛊,穿插各种体例,错乱时态,颠倒梦想,那就是骆以军的拿手好戏。也就是《妻梦狗》以来,“时间之屋”的策略。在时间之屋中,不同时段、生命状态的人被压缩在一起,挤在同一个屋檐下,小说的行进就是时光之屋中房间的漫游,而故事到了最后,故事彼此破窗,破格,在某个不可能接口连接上。
“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像破碎的漂流物,或不同人之间的梦境之序,竟然可以穿透框架,跑到别人的回忆里”
“从一个二维世界挣脱冒出…..然后又窜进另一幅画中”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桥段,被收容山谷的小说家说起自己的故事,是关于香港女孩安。在安的丈夫过世后,小说家照顾他,对安说故事。乃至安有一天跟他说,自己梦见亡夫了:“他就在一片绿光充盈的山谷中”。小说家忽然有此一念,“我们之所以在此相聚.....全是她那良善的念头,一顺之光幻造出来的这绿光盈满的山谷”
这是一个故事的回圈,连还套,站在“之外”说故事的小说家发现,他在对方身上植入一个念,而这个念催动了梦,自己竟可能是被装在这个过了两手制造出来的梦/故事“之内”,最外与最内此时成了莫比斯环相连,那在现实中不可能,却在小说中成为奇观。
这说故事的策略该也涉及他的关怀。
小说家之书写一直有一种敏锐,他笔下总写日常的伤害不停发生,“但只有我知道”。那意味的是,秘密的诞生。从此,我跟人不一样了。秘密带来的是(说故事的)权力,却也伴随痛苦。是诅咒。无人知晓。
这似乎也是骆以军从出登场文坛后问出的著名问题———最里面的房间到底有什么?
《降生十二星座》告诉我们,最里面的房间并不在正中央。而在于封闭性。那是无法进去的,直子之心。
而小说家则在小说中制造不可能的奇观,奇迹,试图寻找、破译那个秘密──进入最里面的房间。而进入终究是不能的吧。可在那歪歪倒倒的终究徒劳的途径之中,我们看到的是,你那么努力了啊,那就是爱之诞生。慈悲之诞生。悲悯之诞生。人性之诞生。
“之外”的第二个层面,从(小说)“之外”来言,也就是和现实的关系,《大疫》中不无指涉的多次指出,“我想许多他的读者,也会习惯性的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混淆了他小说中那些怪异变态的思想模型”、“惯性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混淆他小说中那些怪异变态的思想模型,替他多打开一个超乎正常逻辑之外的抽屉”,我倾向把这视为一个辩解,《大疫》外的小说家也正经历大疫,不,小说该一直就是他的疫,早在更早之前,人们就不停的比附,查核,检查他的作为,核实他的政治倾向和思想,确认现实与小说的重合否,那和他的小说术有关,但作为小说家,他本来该在小说这个装置“之外”,却因此被卷入小说之中。甚至,小说里的他可能比小说外还让人感到存在强烈,小说外的骆以军变得无比影薄,“之外”被“之内”卷入了,现实和小说破开一个口,他的现实被自己的虚构覆写,只要他写作和阅读的行为存在,这个黑洞就不会消失。
我不知道是小说摹写了现实,还是现实模仿了小说。我以为那才是奇观。
综合上述两个层面,“之外”延伸出第三个层次,那吊诡显示,当我们说“之外”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在小说“之外”。
《大疫》中透过小说中人提到:“小姐说二先生说 ‘我绝不会和他们一样’,但后来二先生又说‘我终于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了。’”
当然这句话可以完全在小说文本层面解读。但如果对照上述的“之外”层次之二,“事件”的影响效力如此强力,虽然小说中直面真实世界的“事件”本身空缺了,但是不是正因为小说“之外”的强效,他的催哭/摧枯拉朽,才更巩固上述小说家坚信叙事伦理和小说家位置作为一种“之外”,所以在《大疫》中我们看到故事群、故事聚落、故事的核爆,“并不是疫情来了,我们只好说故事”,而恰恰是“疫情来了,我们因此必须更说故事”,故事本身作为一种隐在的抗衡,上述“之外”的小说伦理作为书写者自身奉行的第一道德圭臬。它的力量,一种道的理念反而更坚定了。
但另一方面而言,小说家又担心,面对“事件”,他是不是终究变成“我终于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了”,我也坏掉了吗?面对暴力,金刚怒目?便又回到那句老话,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著你。
爱的瘟疫
据说《大疫》在前期书名是《爱在瘟疫蔓延时》,成书之时,“爱”不见了。但“爱”又没有不见,小说家在《大疫》中喜言爱。
小说里,这个自称“北北”,这个被社交媒体和政治正确所规训,必须在小说中不停自承自己是“异性恋直男癌”、“充满男性荷尔蒙之意淫”的小说家,没羞没噪的提起爱。但骆以军又岂会不知道,从十九世纪以来,爱已经被资本主义,被戏剧被电影被小说被各种鸡汤文乃致你我的脸书,消磨的差不多了。
爱本身甚至比他贯穿全本小说的心经,更像咒语,更像是迷面。只剩下字面的意思,像是心经一般。
终究,“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被耗尽了。连小说中人物都跳出来说“爱也被属于他的抽象维度之病毒感染”,“爱”被他一直说,却越说越稀薄。
《大疫》中这一页在谈爱,翻过一面小说家就搞起了未亡人你看,又来了。想必所有读者都这样拍额头),“他想爱她”、“但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强暴了她”,在他笔下,性是近乎理解所以身心灵交融,却又无比暴力。小说中男性小说家与安的身体推拒还迎之舞以各种变型散落在《大疫》各事件中,也进出小说家毕生小说中,他总刻意跨过那条线,在伦常、理性、人我关系、社会性眼光之间反复跳跃,辩证,不停自怜又自恨、自问。侠以武犯禁,骆以小说犯禁,犯罪,更犯贱。
小说家在《大疫》中举夏目,举川端,举井上靖举三岛、纳博柯夫等作品为例,那是他年少膜拜的小说,在这些前辈过激作品中(烧了金阁、强暴、坚硬鞋尖踢像肚腹),小说家自承那令他目眩想抵达的是“那非关色境,而是一种‘对美疯魔, 推到极致,停在那火柴棒之火苗将熄未熄之瞬’”
正因为爱被耗尽了──这场大疫也是爱被感染的瘟疫──小说家必须用烧红的铁钳,用磨利的刀尖,或是湿漉漉的臭鸡鸡。他耍宝,他不惜作贱自己,他毁三观,“不可以色色”,他搞变态,既“过激”、“超常”,甚至要去“上未亡人”、“像强暴”、“我丈夫死了,从此我就是人尽可夫的女人”,但在这些情节的展示中,无法预测,不能预料,却又言之成理,在发动的瞬间,包括但不限于,等于更超出,他试图以此重新电极,或发明“爱”这个词汇。
说起来,政治正确一定轻松多了,或仅仅把“爱”字照本宣科念出来。“可那不是我的忍道。”
就算经历那么多,无比痛苦。穷声哀号。就算被人视为野兽。
小说家闷头就是要干,要去干,他总想用小说体现‘停在那火柴棒之火苗将熄未熄之瞬’”。
小说家就是世界中心呼喊爱的野兽吧。
电影《老男孩》里说:“就算我是野兽,野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而骆以军再一次用小说趋近“火苗将熄未熄之瞬”,纵然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实之肉身已经成了火柴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