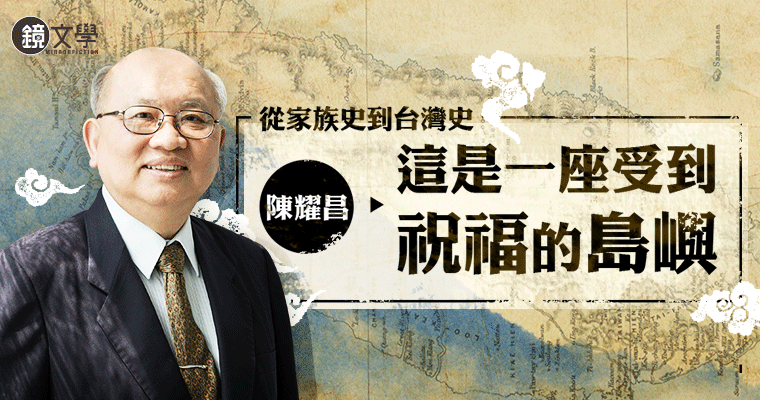
【作家特寫】從家族史到台灣史 陳耀昌:這是一座受到祝福的島嶼
立即閱讀:《獅頭花》 追索家族血脈的故事,是陳耀昌寫作的起點。 他自醫學研究半路出家寫小說,為的是當初聽說陳家祖上有個「荷蘭嬤」。寫著寫著,荷蘭嬤究竟有無,於今對他而言已不那麼重要。他有更大的心願──希望今年(2019),我們的政府官員能夠去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出一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由台灣原住民頭目卓杞篤與美國駐廈門總領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所簽下的約定書。 那是十九世紀中期,發生在恆春半島的事。一八六七年,美國商船羅妹號(Rover)於墾丁一帶觸礁,船員們登陸避難,卻不幸遭當地排灣族原住民襲擊。船員家屬輾轉委託時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前往交涉,促成了李仙得與當時「下瑯嶠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會面,協調原住民日後協助船難者的允諾。 一八六九年二月,兩人再次見面時,卓杞篤要求將先前的口頭約定落成文件,成了台灣第一份由原住民與外國簽訂的外交條約──據信這份文件目前仍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這段歷史,則成了陳耀昌「台灣花系列」首部曲《傀儡花》的上演舞台。 自醫跨文習慣埋頭找資料 《傀儡花》之後,是《獅頭花》。接續《傀》書寫的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年, 重現一八七五年屏東大龜文王國與清朝淮軍之間,那場如今早已被島民淡忘的「獅頭社戰役」。厚墩墩兩部鉅作,出版時間相隔不過一年餘;此前他還有小說處女作《福爾摩沙三族記》,一出手就是大長篇。說起寫作過程,陳耀昌最常掛在嘴上的,無非是他四處踏查田調時所碰上的種種巧合,以及那句總是被他用來作為結論的「如有神助」。 「每次人家提到我寫小說,都說我不務正業。我要特別強調,我才沒有不務正業。我可是很認真在做我的醫學教授。」陳耀昌半開玩笑地亮出衛福部頒發的獎章──這位全台首屈一指的血液腫瘤內科名醫兼台灣細胞醫療先驅,執筆寫起小說,也不過是近幾年的事。 陳耀昌開始寫小說後,許多人開他玩笑說他「不務正業」,其實他另一個身分是血液腫瘤內科名醫兼台灣細胞醫療先驅。 「很多人都問我怎麼開始寫作的。我五十歲之前只有寫過兩次文章:一次是小學五年級的全省作文比賽,我得了第九名,那是我唯一和寫作有關的獎項;第二次是大學時,我擔任台大醫學院學生院刊《青杏》社長。這是我少數與寫作沾得上邊的時候。」講起來都是相當久遠的事。 二○○三年二月,陳耀昌受時任中央社副社長的曾嬿卿邀請,在《財訊》開了生技專欄,一寫就是三、四年,是陳耀昌固定發表文字的起點。二○○四年,一次回台南老家掃墓,叔叔告訴他,陳家在台灣第一代的查某祖是「荷蘭嬤」。「我就想:我自己是做基因研究的,怎麼不試著看看從資料證明我是荷蘭人(的後代)?」 有了專欄「練筆」的基底,加上畢生從事醫學研究,早已培養出埋首文獻資料的無限耐心與功力;驚人的記憶力,更讓任何蛛絲馬跡烙印在陳耀昌的腦海裡,舉凡人名、照片、時間日期,近乎過目不忘,必要時得以串連──凡此種種,都為陳耀昌自醫跨文的鍛鍊做足了準備。 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陳耀昌人在首爾,半夜三、四點睡不著,乾脆起身寫下《福爾摩沙三族記》第一章。「我第一行怎麼寫你知道嗎?我寫:『三到五萬字,中短篇小說。』」起於叔叔不經意的一次談話,讓陳耀昌從家族的追尋,爬梳一六二四年荷蘭人來台後,在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千絲萬縷,最後成了浩浩蕩蕩的長篇。雖然沒能真正證明自己的血脈,然作品出手擲入文壇,卻是一鳴驚人。「我的目的是寫我祖先的故事。後來幸運得了獎,想說不要變成一書作家,這樣太丟臉了。就繼續寫吧。」他說著說著,又是哈哈一笑。 重視踏查藉此呈現多元史觀 寫的雖是小說,然陳耀昌非常重視踏查;親臨現場為他帶來的衝擊,不僅是他創作時源源不絕的靈感,更是他無法停筆的驅動力。許是自身醫學領域的間接影響,陳耀昌的小說主題,特別著眼於台灣歷史上族群間的衝突與融合。如同他在另本著作《島嶼DNA》所聲明的主張:台灣人(種族)很「混」,且早已「混」得都相同。「假如我們從一六六一年鄭成功來台算起,到現在三百五十幾年。往上回溯,經過了十二代或十三代,一個人有幾個祖先?答案是2048或4096。現在的你的DNA,只是那裡面一個人的,你要怎麼證明不同?」這是陳耀昌不時倡導族群和諧的論點基礎。 寫的雖是小說,陳耀昌非常重視踏查,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點,再遠他都跑去現場。圖為原建於光緒三年(1877),位於北勢寮的「淮軍祠」(不知何時改名為白軍營),埋有約四百名未參加「獅頭社戰役」即已病逝台灣的淮軍。 台灣是移民社會,隨時有人來來去去;台灣人的「混」,是地理與歷史造成的必然。也因此,陳耀昌認為,讀台灣史,需如陳寅恪所說:要有「了解之同情」。 陳耀昌寫《傀儡花》,寫《獅頭花》,寫原住民、漢人、清朝淮軍之間的糾葛,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點,哪怕可能只是一座破敗的小廟、偏遠的孤墳,再遠他都跑去現場,試圖感受空氣中遺留下的氛圍。「我們常說漢人欺壓原住民,或說原住民襲擊漢人,其實不能這樣講。一邊是冒死過來求生存,一邊是受到侵犯。但這就是移民社會的無奈。」清朝實施海禁,中國沿海居民迫於生計,只得冒死渡過「黑水溝」,所謂「六死三留一回頭」,成功率只有三成。「大家都有為了求生存的不得已,不然要怎麼活下去?」 「所以我才強調『多元史觀』,特別像我們這樣的移民社會更加需要。要兩邊互相體諒。但這很難。」陳耀昌認為,要解決族群問題,必須先相互了解歷史。畢竟各有處境,端看各自理解的角度。 然這樣不是雙方各打五十大板嗎?「你要說是,也許吧。但要這樣才能族群和諧啊。」人生在世,誰都不過圖個安身立命,但能不能在互知互諒的前提下,做出最大的轉圜?「台灣的族群混雜是事實。族群當中,我們可以分出各自的文化,那是多元;而族群的確有人數多寡,我要強調的是『同舟共濟大和解』,包括一九四九年過來的人也一樣。用俾斯麥的話:愚者向經驗學習,智者向歷史學習。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為小事情擦槍走火,在這個時代,我們更要避免同樣的狀況再發生。」 小說化歷史補足台灣史空洞之處 《獅頭花》企圖重現一八七五年屏東大龜文王國與清朝淮軍的「獅頭社戰役」。圖為位於台東達仁鄉的大龜文王國標示。 縱使陳耀昌後來的書寫,已與追尋家族血脈無關,然他依舊孜孜不倦,要說他轉而追尋「台灣史的血脈」,也無不可。「我自認我寫的是小說化的歷史,不是歷史小說。台灣史有太多被誤解的、空洞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補上。就像吳密察說我是『另類的歷史書寫』。他承認我寫的是歷史,不是憑空編造的小說。」以小說為手段,替「如何理解台灣歷史」下一帖藥方,正是陳耀昌的目的所在。 「台灣一直是被上天眷顧著的。台灣歷史上從來沒有大規模戰爭,土地下的冤魂,為數甚少。當然要去理解對方、對不同立場的人感同身受,是一件困難的事;也從來沒有一個地方像我們台灣這樣,無論從民族、歷史、地理等觀點來看,都這麼複雜。但我們是很特殊的。這是歷史給我們的優勢。」即使每一段台灣史讀來、寫來,處處都是艱辛困苦,陳耀昌依舊懷抱樂觀,「我一直認為,我們是被祝福的。Be blessed。」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