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的有罪論──蔣亞妮讀《親愛的共犯》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裡,寫下:「我們在沒有被忘記之前,就會變成一種媚俗,媚俗是存在與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點。」陳雪的新作《親愛的共犯》逼近的核心,與它相近。與其說,這是一部懸疑小說、推理小說,其實它更是藉著一場綁架失蹤案、借道小說中住在「白樓」裡外的眾人,將視線投向「媚俗」世間。像是以燈探照,什麼是好、什麼是愛,你的心真的為此震動嗎?《親愛的共犯》陳雪 著出版日期:2021/1/29與前作《無父之城》相同,故事始於一場失蹤。這一回,住在「白樓」裡顯貴的張家三代,二子張鎮東忽然被綁架,刑警周小詠展開調查。嫌疑者有財富、有愛情,當然也有妒恨,人類究竟會被什麼驅動?當我們關心一個社會案件、當我們為了家人與愛情付出、傷痛、流下眼淚時,要怎麼看待每一滴眼淚?眼淚,總有兩種,第一種眼淚,是出於自己與對方的關係;第二種眼淚,卻是因為彷彿能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同悲憫共感動,如此美好豐沛,流下的淚。兩種眼淚,都是愛,或以為是愛。這也是米蘭·昆德拉告訴我們的:「地球上人的博愛將只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如果可能,請把這本小說裡所有的眼淚與選擇,看作第二種。只因為,這個世界目前的眼淚,都更貼靠後者。複調之式神陳雪的小說總像是課堂裡沒教的文學核心。奇技淫巧與理論形式,那些可以被書明、曾經被論述的典籍,先變作了小說作品(work),再變成我們所見真正的文本(text)。從作品到文本的逸變,是一種精神視線,作品是可見的,文本是不可見、不可被計算與評價的;作品會佔據空間,文本則是一座方法場,我們只有透過創作過程,才能檢驗文本。曾有個被單一化到極致的人物,那位像是一生只說了一句「作者已死」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其實他所知更多:「文本不只是符碼、可見的物件,更是烏托邦、不可見及一個可流動的過程。」如此看向陳雪小說的軸心,尤其到了《摩天大樓》與《無父之城》後,更能理整出她小說的特長之處,課本裡、理論上、簡而化之的一個名詞:「複調小說」。西方世界,從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威廉·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的小說到《冰與火之歌》;東方與之相對,亦有《羅生門》及上溯至《紅樓夢》、近身如湊佳苗小說般的複調藍本。於陳雪的小說中,不管是此本《親愛的共犯》裡,間次地以失蹤者張鎮東身邊之人開章分述,從引夢辦案的刑警周小詠、生於微處的張鎮東妻子崔牧芸、張鎮東的大哥大嫂,到白樓裡的管家陳嫂、外傭阿蒂⋯⋯全都成了陳雪指點江山的各種樂音。一如她在《附魔者》裡,似以魂力捻出燭繩般,點燃所有在愛中的不同傷者與叛者⋯⋯直至《親愛的共犯》,讀者終於可以篤定知曉,小說家完全自知她與她的小說之技,有著如陰陽師與式神般最強大的契約術法,不論是複調、懸疑與人性,她都握於掌、曉於心。大象灰色的夢遊者小說和愛情總是相近,最近之處,是明明知道所有的道理、做好一切準備,卻還是寫不好一本小說、談不好一場戀愛。這便是「複調小說」一詞,在課堂外的核心,在陳雪手中的別樣,更是陳雪在經過了幾年的文學高強度寫作計畫(字母會)後,意外地,將她的自我與小說濃淡度調低,從墨黑漂成了大象灰。小說中幾次以顏色寓階級,先是「白樓」那難以言說的白之綜合:「只見得一片雪白、粉白、霧白,紛紛落落地營造出一種濛濛的光暈,陽光底下看起來,眼睛都要閃痛了。」再來便是「大象灰」,「這世上竟然有某些顏色是昂貴的⋯⋯大象灰,聽起來不起眼的名字,那灰色若不是使用高級皮革,並且透過特殊的調製鞣製印染,不可能呈現出來,沒有經過複雜的工法,最後只會變成老鼠灰。」陳雪的小說便似那法國最奢靡的皮革名店,凡俗者總被滿櫃的時裝或前頭的金工珠寶所誘,可那以Madame小牛皮、Epsom牛皮精巧鞣制而成的大象灰或班鳩灰,穩當地收在暗架,必得等候暗語、確認眼神,才能成為那識貨人。它才是每個名字後的一生歷練,如玉髓、岩腦與樹之琥珀。這本《親愛的共犯》可被視為影像的衍生空間,另一部獨立於陳雪「空間三部曲」中「大樓」(《摩天大樓》)、「小鎮」(《無父之城》)、「海島」(尚未出版)寫作版圖外的作品。雖然,小說也極大程度的貼著「文明街四十五巷」那座白色大宅的空間伸展枝枒。但陳雪大幅地縮砍獨白與囈語般的文字句式,把枝枒留給顏色、形貌、建築與故事情節,這使得它的文字也變得近似一座建築。透過指令、聽聞線索,讀者便成為了觀眾,小說中長出樓宅、看見人影,影視化的野心由此可見。沒有野心的書寫,難以成就偉大的作品與作家。每當作家一開始寫作,作品就脫離了他自身,從陳雪的寫作段落中,偶爾剝離如降靈般的感受,比如寫夢論夢,醒覺而別緻。小說中能以夢探案的刑警周小詠,這麼說起她的夢:「如今的夢,都像是白天工作的延續。」、「她知道這不是託夢或什麼神奇能力,這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她思念父親、努力破案,兩者合一,就成了夢裡辦案的情節,但這就是她想要的。」在這裡,夢不是神諭,夢是野心。小說家和刑警和世人相同,自以為通透如解夢者,皆為夢遊者。正如寫出《他們》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喬伊斯·卡羅爾·歐茨(Joyce Carol Oates),這樣定義作家與夢的關係:「我們也許沉溺於夢境,但絕對不是出於對現實的恐懼或者篾視。我們寫作的原因與做夢如出一轍,我們沒法不做夢。寫作的人是嚴肅的做夢者。」這是一部推理小說,小說理所當然的推向了犯罪者的謎底,卻提供了另一個思考與暗號:「有罪等於可恨嗎?」同時,這也不只是一部推理小說,因為它不斷給予提示,幾近心理暗示。翻開書頁,小說之前,你首先會看到「天空是白的,但雲是黑的。」這是出自經典法國電影《新橋戀人》裡的一段台詞——它更是確認彼此相愛的密語,雖然大多數的愛情,總是危顫、瘋癲與不公平的。愛這件事,果然與小說很像,可能罪惡,卻不一定可恨。本文作者蔣亞妮1987年生,台灣台中人。 摩羯座,狗派女子。無信仰但願意信仰文字。東海大學中文系、中興大學中文所畢, 目前就讀成功大學中文博士班。 曾獲台北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文化部年度藝術新秀、國藝會創作補助等獎項。2015年出版首部散文《請登入遊戲》(九歌), 2017年出版《寫你》(印刻), 2020年出版《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悅知)。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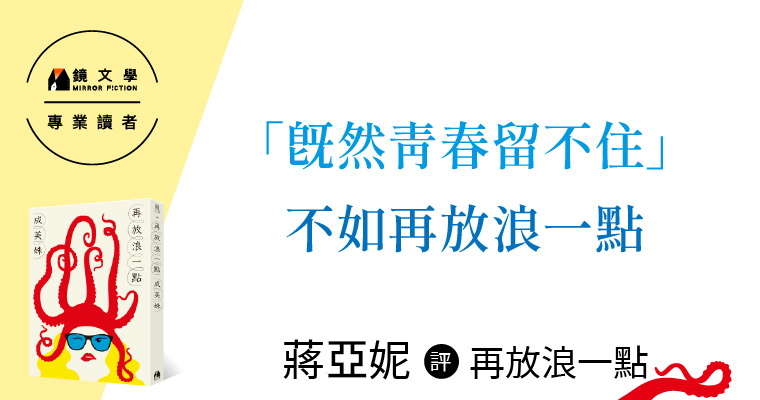
「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再放浪一點——蔣亞妮讀成英姝《再放浪一點》
我很害怕單一化。不管是一件事、一種稱呼、一個版塊或一類性別,比如「女性文學」、「女性作家」與「女性書寫」(替換成同志亦然),但我明白這些存在,依然有其必要性,因為世界確不存在專指男性書寫的「男性文學」,我們只能不斷催熟「其他」、壯大「之外」。《再放浪一點》成英姝 著 出版日期:2020/6/12成英姝的最新長篇《再放浪一點》,距前作《寂光與烈燄》整整四年,男賽車手開出記憶的荒漠,這次的小說主角是三個有欲望、有野心的女性。成英姝只使用了一個進行中的「劇本」,便將三者串連。三十多歲的女編劇高愛莫,一直期待寫出暢銷劇本,卻總是心比手高;五十多歲的過氣豔星鞏麗蓮,將最後翻紅的機會壓在請高愛莫為她打造的劇本上;最後是二十多歲的Z咖女演員林由果,為了演出機會極盡賣傻、賣瘋、賣性感,拋售羞恥。不經意處,有著張艾嘉2004年電影《20.30.40》的女性年齡思考,或許一點1994年王晶電影盛世時期《戀愛的天空》(又作《四個好色的女人》)中的自覺與譏誚,偶爾閃過2013年黃真真執導的《閨蜜》裡,少數精彩大膽的生動對白,疊影混搭。說穿了,《再放浪一點》是講女性的小說,卻不該被單一化為女性小說,這是我深以為戒的閱讀整理。1990年「布克獎」得主,英國作家A.S.拜厄特說過:「如果要做為一個好的女作家,你首先要是一個好的作家,而不是僅僅和女作家在一起,大家只討論女性的事情。」這與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說過的:「在這個世上,我首先得是一個負責任的父親,然後才是一個作家。」放在一起看,相當有趣。事情的優先順序永遠是,先是一個怎樣的人、才是一個怎樣的作家,至於性別,萬萬不需要淪落為少數族群與偏遠地區一般的加分要點。成英姝雖然在《再放浪一點》不斷拿針戳出女性的血點,像是談到年紀時,她寫四十多歲女人的屁股,會從短褲下緣垂出,但穿的卻不是熱褲;可四十多歲也不全然缺點,比如女人拉皮:「都說拉皮就要趁年輕,大概四十多歲最好,拉了能定型,還好看,老了才做,三兩下就崩壞了。」幽默的最高級是開自己玩笑,這點成英姝與她小說中的三個女人都做到了(換成男性處理就容易落得政治不正確)。如果就只停留在此,三個女人一台戲,就算再加上一個暢銷名作家梁夢汝與時尚設計師維若妮卡,五個女人大搞女性主義,唱得也還是過於單調了。還好,成英姝不需要女性加分,她在《男妲》跟《地獄門》等長篇作品裡,已經自證這點。不管是暴力、類型、情色與異色,她都玩過了,所以我們必須看進深處,穿越性別、翻玩意識。大家應該都聽聞過維吉尼亞·吳爾芙那如當代夏娃宣言般的「自己的房間」,女性(尤其寫作者)要有一個自己的房間,房間需能上鎖。不過吳爾芙的原句不只這些,而是:「女性要想寫小說或詩歌,必須有五百鎊年金和一間帶鎖的房間。」散文集《自己的房間》出版於1930年前後的英國,作個簡單計算,那時的500英鎊約等於如今的120萬至150萬新台幣(相近當時英國中產階級以上男性年收入)。吳爾芙與她「500英鎊說」也非憑空發論,剛好是她姑媽留予她的遺產年金。可惜,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民國107至108年平均年收入,當代台灣女性大約落在57萬至60萬間,小說中的三個主角大約也不會超過這個數字。當我們都少有「500英鎊」年收時,就不再寫了嗎?答案很簡單,不管你是男是女、優渥還是落魄,都得要寫。反正生活再慘,小說裡得暫時靠海苔片、泡麵、豆腐撐過生活的女編劇也寬慰自苦地說了:「幾個月接不到工作,明明過著清貧的生活,卻一點也沒瘦,又是一樁宇宙並非邏輯建構的證明。」編劇也好、作家也好、畫家編輯老師都是,拿著筆的一個都逃不了,比起性別,《再放浪一點》的主體,更靠近一群無處可歸、無路可出的現代人。這不禁讓我想到多年前成英姝在「三少四壯集」發表的短文〈我們都太在意永遠〉,她寫喜歡的作家:「托爾金的世界是一個放置在真實的凡俗的平淡無奇的世界中的箱子,兩者平行重疊,當濃霧遮蓋了視線,有時撥開那白色的簾幕,就會置身在托爾金的世界中。有一種電影情節,主角意外或者為了某種目的,來到了另一個時空,大部分的劇情,最後都讓他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這也是我在讀這本小說的感受,當我在小說世界、他者時空,遊歷一場後,卻發現聽到的全是我自己世界的回音與困境。比如,故事的存在可能;比如,美好的總是往日時光。雖然美國小說家勞倫斯·卜洛克聲明:「偽造正是小說的核心與靈魂。」而在一眾台灣小說家中,成英姝很高程度地展演了她虛構(Fiction)的能力,私小說的座位,即使你拿著她生平門票一幕幕尋找,最多也只能看見經過了離解、脫墨、洗滌、漂白而還魂的再生紙,前人的名字與筆跡,你找不到。她是罕有地認真說故事的人,為我們展演她精心設計的一個又一個「靈暈」(aura)。靈暈就像故事的入場卷,你得透過它才能真正進入故事氛圍。她通過小說中編劇角色的困局,狠狠敲擊了當代文學一直討論不休的:該怎麼說故事、還有沒有故事,以及有沒有人還在說故事?於是在小說故事完結前,她忽然花了許多段落定義「故事」:「故事究竟有沒有它自己?那個它自己又是什麼,在什麼時刻誕生的?人的一生說了數不清的故事,這些無窮的故事散亂,充滿矛盾、歧義,它們會被什麼指向一處,變成同一個故事嗎?⋯⋯事實上,每個故事在當下便已完成了,每一個瞬間就涵蓋了過去和未來的可能,在那個點上,它已經是完整的了,有它自己的內在邏輯。」成英姝以故事作答故事存在,故事是有可能的,小說依然在說著不同故事與包裹故事,故事裡又再藏著些許內在自我。小說隨著主線「劇本」的完成,走向結尾,最聰明者顯得蠢笨、最癡傻者卻看得最清,撕逼的人說不定相知相惜,這樣的安排在小說裡並不特別,特別之處是成英姝洞悉世情的口吻,當她寫道別人教訓愛莫的編劇態度時,說的是:「你犯的這個毛病也反映在你的創作態度裡,你鄙視陳腔濫調,你對於無論是別人或者自己曾經說過的話都認為沒有價值重複,但你以為真理有多少?」過去了,才有來處可以回頭,天真過,也才能說世故的語言。我和小說同時驚覺,現在的所有故事,都由「過往」觸發至今,就像五十多歲的昔日豔星高談自己仍有粉紅色乳頭一樣,看似放浪的全是幻夢。每一個小說的角色都困於舊日,尚未發福的身材也好、捧在手心的愛或是充滿可能的未來都結束了,於是小說為他們寫下:「以為永遠記住我們年輕時的樣子,彷彿就能回到過去,但過去就和未來一樣,從不在默默那裡等待。」說的其實是,往日時光,早已遠去。「回不去」的不只叫半生緣,方文山為南拳媽媽寫的歌裡,那年Lara也唱著:「到不了的都叫做遠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鄉。」小說中的每個人,似乎也都無家鄉、無歸途。既然無家無鄉(也沒有吳爾芙說的百萬年金)、既然青春終究留不住(也活不成李宗盛一樣的成功大叔),成英姝告訴我們,不如再放浪一點,反正,沒有從前了。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