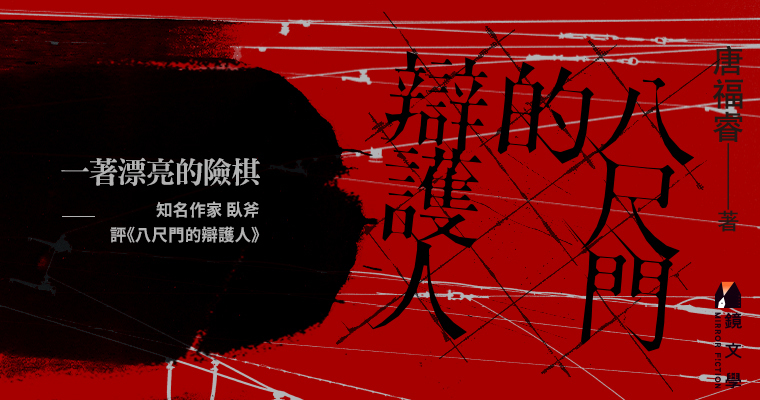
一著漂亮的險棋──臥斧評《八尺門的辯護人》
倘若有個出現「謀殺」情節的故事,「誰做的」、「怎麼做的」常會是故事裡的主要謎團,尤其是傳統推理故事,解開這兩個謎團就可以滿足閱聽者,結束故事。這兩者會成為主要謎團的原因,在於謀殺事件發生的當下,很可能只有凶手與被害者在場,事發之後凶手不坦承、被害者無法言語,它們就會成為偵破案件的關鍵。現實當中的謀殺大抵也是如此,只是或許不像虛構故事那麼複雜──特別是「怎麼做的」這部分,極少牽涉到精巧華麗的機關或天衣無縫的計劃。但是現實當中解開謎團並不會結束故事,還得進入司法程序,而刑罰裁量其實是更複雜的環節──除了確認凶手是誰、如何犯案,還得探詢犯案意圖、案發經過等等,才能進行裁罰,凶手與被害者的關係、社經階級,甚至是社會觀感與政治氛圍,都會或多或少影響審判,更別提有時進入庭審程序之前,凶手身分根本還沒完全確認。由此看來,《八尺門的辯護人》走了一著險棋。《八尺門的辯護人》唐福睿 著出版日期:2021/12/10故事描述父親曾因殺人入獄的原住民公設辯護人佟寶駒,在預備轉職到薪資條件更優渥的律師事務所前夕,因故參與一樁移工殺害船長全家的滅門血案;佟寶駒原本並未太過投入、打算應付了事,卻在熱心於廢死議題的替代役男連晉平從旁推動,以及獲得來台幫傭的印尼女孩Leena協助下,開始發現案情似乎並不單純。假若將《八尺門的辯護人》視為推理小說,讀者的確可以從情節裡頭獲得推理樂趣──蒐集線索、拼湊證據,逐步重建案發現場;書中法庭攻防的橋段描寫詳細、手法巧妙,在國內的作品相當少見,作者唐福睿的律師實務經驗想來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不過,唐福睿並未將焦點完全放在營造推理趣味上頭。事件發生與當事人的個人本質有關,也與當事人之間的情感或金錢之類連結有關;放大點兒看,當事人的狀況會與成長經歷、生活樣態、家庭環境、社經位階等等有關,而這些東西又與時代背景、社會發展、經濟局勢、政治意識,甚至國際關係有關。大多數的故事情節都依附著角色前進,隨著情節開展,閱聽者會逐漸明白上述種種如何與角色的個人特質結合,並且在角色決定如何面對事件時產生催化或嚇阻作用;也就是說,雖然情節依附著角色前進,但閱聽者或多或少可以從角色的遭遇裡明瞭故事當中包括時代與社會等等情況,倘若創作者處理得當,那麼閱聽者就能獲知更全面的社會樣貌。《八尺門的辯護人》中角色分屬不同族群與社經背景:佟寶駒是一心想脫離傳統聚落與階級的原住民,連晉平是來自法學世家、也準備從事法律工作的司法新鮮人,Leena是受過高等教育但來台從事勞務工作的弱勢移工;遇害的船長一家是與佟寶駒相同聚落的原住民,受僱於漁業公司,漁業公司的勢力除了掌控原住民船員及教育程度更差的移民漁工之外,也藉由政治獻金等等管道與政府產生關聯。而政府單位就是國內的權力機構,與司法系統直接相關,加上選舉考量及輿情風向,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左右審判過程。是故,《八尺門的辯護人》主軸雖是以移工為凶嫌的滅門血案,但唐福睿描寫的不只是對一樁案件抽絲剝繭的調程經過,而是整個社會的概略全貌──因為如此社會結構產生的種種利害關係及族群之間的相互傾壓,才會釀成這樣的一樁案件;讀者應當注意的,也就不只是「誰做的」、「怎麼做的」而已,還有從角色一層層向外擴延的牽扯,甚至是來自不同國家或過往歷史的遠因。罪案常是時代與社會現象的縮影。罪行本身(例如殺人)並沒有因為時空不同而產生本質上的變化,但「怎麼做的」會與時代有關(例如得要到發明火槍之後才能用槍殺人),而「為什麼做」就更可能扣接時代與社會,反應出那個時空的特色。什麼樣的時空背景才會有什麼樣的罪案,而生活在那個時空背景當中的所有人,面對罪案時的態度或許都不該只有「把真凶找出來」這麼簡單;光是這麼做,遠遠不足以「伸張正義」。因為那個時空背景催生了罪案,所以罪案其實與所有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有關聯;思索罪案反應的各個層面,忖度不同的改善方式,釐清種種相關資訊,或者,至少不要成為將事件朝錯誤方向推擠的輿論之一──假若希望自己生活在一個制度更完善、更能維護正義的社會,這些才是面對罪案時該有的態度。這是《八尺門的辯護人》值得一讀的原因。讀者將在小說結尾得知真相,但也會因此對書中角色的應對手段是否合宜產生疑惑──這是好故事具備的特質之一,不是提出答案,而是透過故事呈現創作者觀察到的問題,提供閱聽者思考的方向。以《八尺門的辯護人》而言,還有另一層更值得讀者思考的意義──因為這個故事的背景,就發生在現在的台灣。保持了閱讀的趣味,描繪出社會樣態並刺激思索──《八尺門的辯護人》是著險棋,但唐福睿這招漂亮。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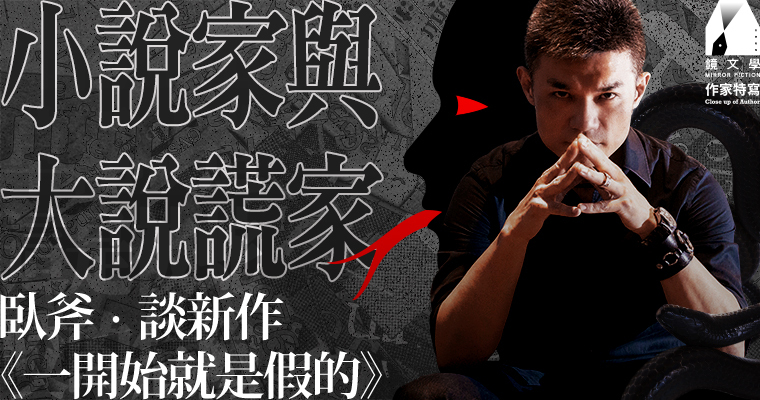
小說家與大說謊家——臥斧談新作《一開始就是假的》
「我筆下的主角常常看什麼都不爽,不怎麼合群,所以很適合衝撞體制。」臥斧如此形容他小說中那些「發覺生活有哪裡不對勁,所以開始探頭找尋真相」的主人翁。 「也很像冷硬派的偵探。」這形容似乎也指向他自己。《一開始就是假的》臥斧著寫小說抬起屁股敲門去有人以「推理一匹狼」比喻臥斧。除了伴隨冷硬派偵探的踽踽獨行,還有看準目標便緊咬不放的決心。2014年以來,臥斧的小說都瞄準議題,「碎夢三部曲」以都更、移工、宗教團體為主題;《FIX》則與廢死聯盟和冤獄平反協會合作,改寫台灣冤案。到了新作《一開始就是假的》,顧名思義,探討假消息當道,濁世何清。套句卜洛克在《八百萬種死法》說的:「辦案本來就是這樣。抬起屁股敲門去。」想找出答案,就認份起身,挨家挨戶敲門找線索。寫小說,當如是。臥斧對寫小說有很清楚的輪廓與目標,「小說是我希望跟大眾講話的東西。我不想製造門檻,而是最大化讀者。因此,讀我的小說不用太傷腦筋。然而,這樣的作品背後仍需要很精密的計算或想探討的議題。」這時,服務生端上臥斧點的熱美式咖啡。臥斧順水推舟的給了我一個比喻,「寫小說就像眼前這杯美式。端上來之前,我得選好豆子,再烘好磨好,同時顧及壓力與水質。每個步驟都謹慎有意義,但我不期望每個讀者都能明白每個步驟的用意。單純把我的小說當作搞笑諷刺也很好。」因此,小說是手段,不是終極目標;它沒有一定樣貌,端看讀者怎麼接收。▲臥斧說自己的主角大多不合群,像冷硬派偵探,才能衝撞體制,說的似乎也是他自己。(圖/鏡文學)出版之後你影響了誰?臥斧像獨行的狼,也跟他的小說策略與所處文學場域有關。1999年他出版第一本書《給S的音樂情書》,便決定不再出版,「我進出版社工作後,對出版的想像與文學獎都有了大概認知。文學獎經驗反而讓我充滿疑惑:『為何這些人有資格評出哪些是好的?標準又是什麼?』2003年是我最後一次參加文學獎,當時投稿的作品便是後來成書的《舌行家族》,決審會議有評審說這作品是一篇鄉野傳奇。然而,鄉野傳奇只是《舌行家族》的外殼。」《舌行家族》真正要談的是話語權被操弄、壟斷——總有一群人,總被一群人把持。諷刺的是,或許也似臥斧對文學場域的心得。之後臥斧有一陣子把寫好的極短篇放在自己架設的網站上,有電子報想刊便隨之取用。不以出書為目標,不參加文學獎,也不在副刊發表,在台灣文壇簡直是自斷雙臂。然而這幾年臥斧創作能量豐沛,陸續出版。對此,他說,「我要服務的對象很清楚,就是讀者。要讓他們讀了不會覺得浪費時間。」「能複製、散布的文字作品不是被藝評家炒作出的單幅油畫,不能想像只有一兩個富豪會收藏會看,必須想辦法讓更多人看見。閱讀也是一種休閒。」更重要的是,「你的作品影響了誰?」這個轉變確立在2014年的《碎夢大道》。「《碎夢大道》後,我開始想寫跟台灣有關的作品,動筆之前我注意到國內很多地方發生火災,可能是老社區或舊市場,印象中大家會覺得這很正常。後來才發現,某些失火市場根本查不出原因,即使新聞提到可能有人縱火,也往往沒後續,這讓我起疑。2007年我寫完初稿,之後看到火災新聞都會特別留心,結果近十年全國有百起相關事件。2012、2013年土地正義議題浮上檯面。我發現這跟我想講的有關——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的拉扯,於是我重寫《碎夢大道》。」「寫小說要想著,這是只有我才能寫出的小說。」臥斧總結。因為「我」在意,因為「我」想找出答案。這個「我」既是他的小說主角,也是他自己。都只有「我」自己,可曾感到孤單?臥斧說,創作本就是孤獨的事,「同時,創作是我覺得最爽的事,我工作就是為了創作,有穩定的收入才能寫下去。常有人問我,為何能穩定的寫?答案很簡單,如果我不創作,其他事就會失去意義。」▲「我不在乎別人怎麼定義我,因此沒有殷切的需求寫一個東西獲得肯定。」臥斧寫東西完全是為了自己,極有規律,他說辛苦工作就是為了有寫作的餘裕,若不寫就失去了生活的意義。(圖/鏡文學)影射政治諷後真相時代寫是為了讓人生有意義,然而「意義」在當下卻顯得曖昧不堪。後真相時代,追尋真相的小說家,是將遍尋不著還是虛晃一招?循此,我們到了《一開始就是假的》。小說緊貼當下政治現實,以死亡議員屍體下葬後卻出現在海濱開場,帶出白黨新興政治明星「韋朝」的崛起,以及白黨過往統治台灣的血腥歷史。此中真真假假,死去的歷史與活生生的現實相混,道盡了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虛妄。諷刺的是,小說主人翁是八卦小報編輯,結果卻是由他來尋找答案。為了銷量,他煞有其事的編造報導——死亡議員握有白黨秘辛,一旦揭露將動搖黨本。「一開始就是假的」怎知卻越演越真,報導提到的人物一一橫死。「主角是本該知道真相的人,卻製造假消息。這本小說與《舌行家族》有關,主人翁都是掌握話語權的人,這一本問題更進一步:掌握話語權的人說謊,我們該怎麼辦?」《舌行家族》寫於2006年,時隔14年的小說卻能映照台灣當下。是歷史太諷刺,還是我們毫無進步?臥斧表示,小說於2018年選舉後動筆,其中人物包括議員佘總、市長韋朝,乃至白黨,都可輕易連結現實中人。寫作當下正是影射人物風頭最健時。時隔一年多,這些人物從無地起樓台到眼看他樓塌了。臥斧或許會說,歷史很滑溜很狡猾,不要想抓住它。這也是臥斧不直接寫明人物的原因,「不能拿小說按圖索驥現實,或指證這就是作者的意圖。如同很多殺人魔或炸彈客,都會說自己是受沙林傑啟發。我們不能完全相信一個人所宣稱的。」焦慮現況那就努力改變到頭來,《一開始就是假的》便是一個聰明的演練。小說確實一如其名,然而臥斧說,「當讀者發現『獲得的訊息可能是操作過的』,後來在接收訊息時,就會停下來思考。我公司的工程師讀了《FIX》,跟我說他以後看到社會新聞都會想一想。那時我想,這就是小說的力量。」「如果人們一開始就發現自己被洗腦,一切是不是就會不同。」歷史沒有如果,所以臥斧變出一條很像歷史的蛇,要讀者感受被咬。很痛,之後會免疫嗎?或許不會,但至少能試著學習教訓。「我很實際,如果你對現況焦慮,就努力用別的方式讓大家看見對的另一面。」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