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特写】谋杀与创造之时──编剧赖东泽与他的地狱全景图
文| 陈黠因、翟翱
2017-0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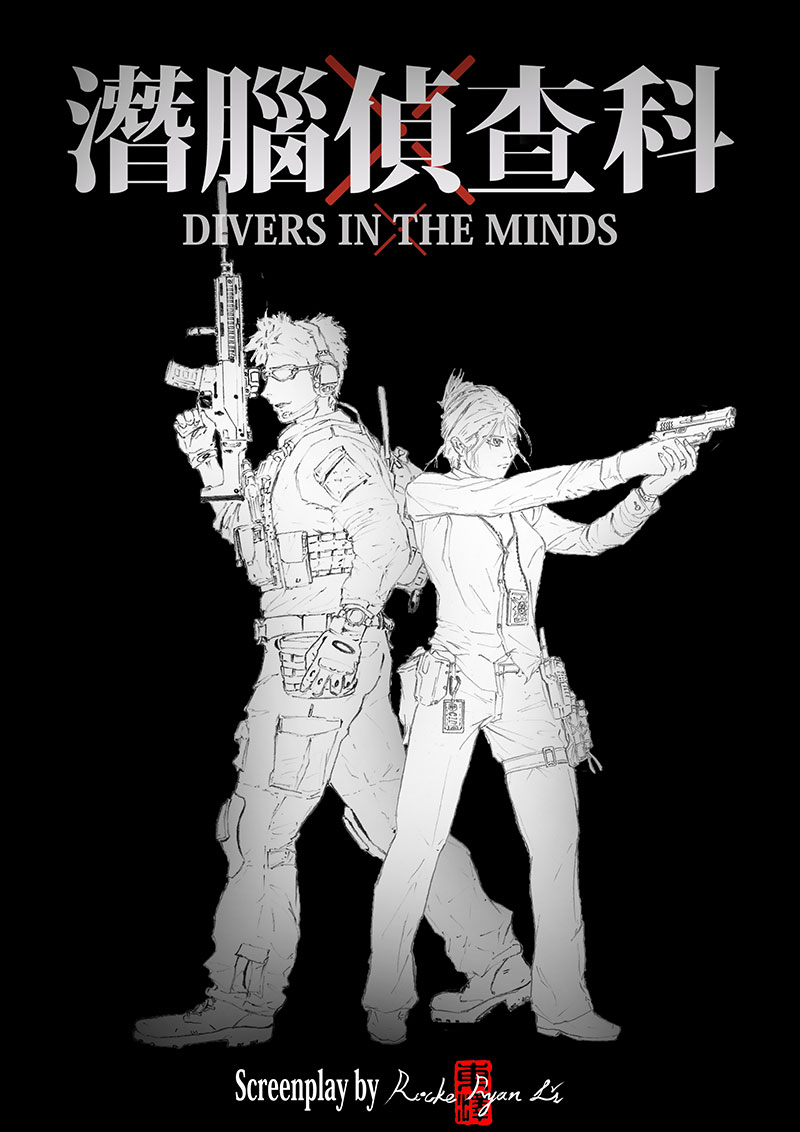 地狱是一种概念,事实上它比口头所谈恐怖多了,而且有千百种样貌,但绝对不会超乎想像,毕竟「地狱」原本就是由心而生。
地狱是一种概念,事实上它比口头所谈恐怖多了,而且有千百种样貌,但绝对不会超乎想像,毕竟「地狱」原本就是由心而生。
地狱,是不可描述的,之于凡夫俗子如你我,是庙宇中的图样浮雕,是长辈要囝仔人隐恶扬善之规训所在;之于大文豪三岛由纪夫也难以描述。他曾以香港的虎豹别墅为例,谓其丑恶宛如抽鸦片产生的太虚幻境。
地狱之于编剧赖东泽,却是日常风景。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毕业后,他专职写作,曾入围皇冠大众小说奖,并以《潜脑侦查科》获得金穗奖剧本优等奖。
绝对在地的硬派之作
《潜脑侦查科》讲述女警探携手「非典型心理学权威」,藉由潜入死者脑内挖掘死因,并试图找出一连串死亡案件的凶手──诡异的是,死者都死于自身最恐惧的事物。所谓非典型,是指这位心理学权威有俗称多重人格的解离性人格疾患,内在高达九个人格,亦正亦邪,有男有女。
至此,你可能想到好几部好莱坞电影,但在赖东泽笔下,《潜脑侦查科》是不折不扣的台湾故事。他让这座岛屿的社会现实与政治黑暗相互纠结,在骇人的虐杀情节之外,更可怕的是我们竟生活在这样的岛上。
这个深具野心,以至于让你忘记这竟是来自台湾作家的剧本,是这样开头的:在锁炼声、古代木齿轮声、火焰声、沸水声、砧板剁刀声、尖叫声中──镜头让观众看清这正是菜市场──一名角色发现自己取代了猪羊鸡鸭,成为待宰的「菜人」。刀斧就要落下。这里正是他的地狱。
魔法爷爷打开了开关
地狱何以成为赖东泽反覆渲染的主题?这要从他摆荡在「信」与「不信」的童年说起。
「我爷爷是道长,在地方上颇有声望。那时,乡下有小孩子一直哭,哭到累,发炎、发烧。我爷爷一去,发现是米缸的位置出了问题,便垫了一颗石头,在米缸里摆了一张符。三天内,那小孩子就好了。这件事记录在地方乡志。当时我念历史系,历史系要做家族史。我回关庙调查,才查到这件事情。」赖东泽说。
赖东泽的爷爷开启或者说动摇了他对现实幻化的可能:「小时候要酬神,爷爷叫我过去,告诉我纸人会跳舞,便拿桃木剑在上面划;剑柄一朝前,纸人就开始跳舞。」赖东泽不信,用手在四周划过一圈,发现没有任何机关。此后,他愿意相信世上那些我们不相信的事。
赖东泽彷彿生来就具备「吸引怪咖」的磁场。他说即使走在寻常街上,也会有老太太靠过来对他说:「你相信电波武器吗?」
那么你呢?你相信吗?赖东泽这样回答:「就数学机率来看,如果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机率不等于零,由于时间是无限的,那么,这件事就百分之百会发生。」听起来近乎诡辩,但赖东泽有更深的体悟。
在幻觉中寻找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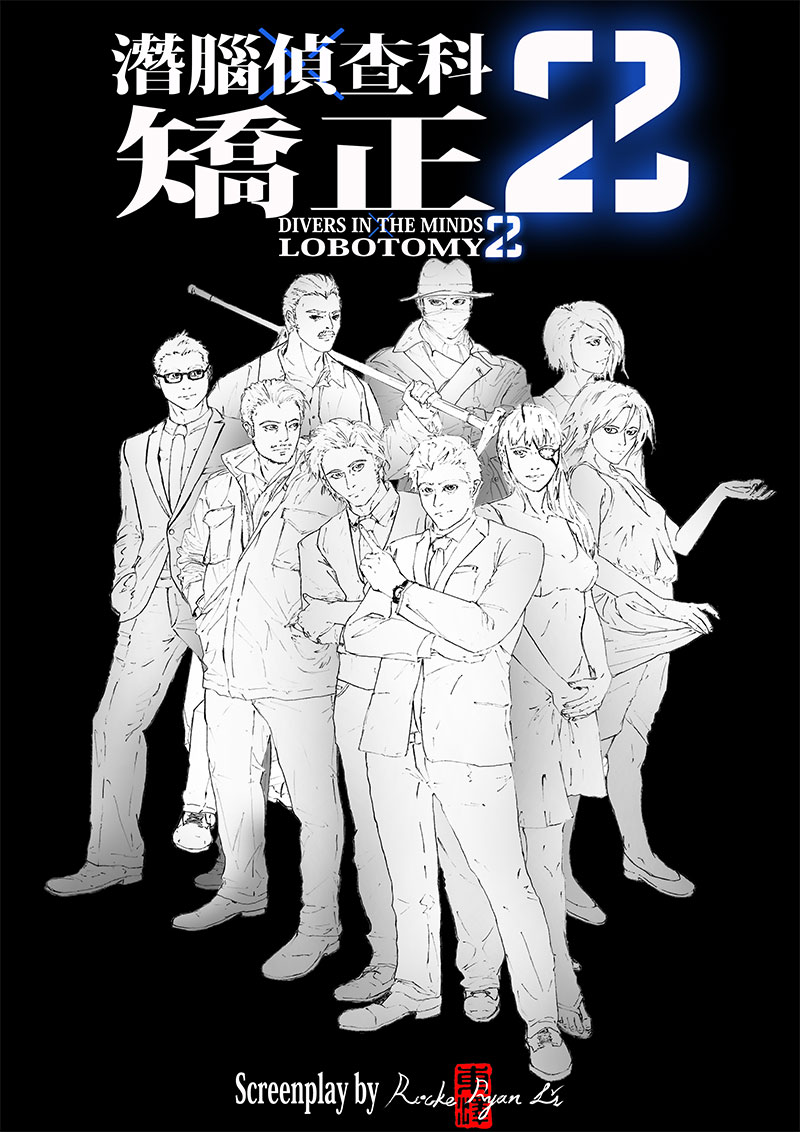 离「被自杀案件」终结已过三年,士宗代替嘲风的位置继续担任潜脑治疗的工作。此时,一起俄罗斯运输机入侵台湾领空的空袭,拉开了一连串恐怖攻击的序幕……
离「被自杀案件」终结已过三年,士宗代替嘲风的位置继续担任潜脑治疗的工作。此时,一起俄罗斯运输机入侵台湾领空的空袭,拉开了一连串恐怖攻击的序幕……
之所以在地狱里恍惚的活著,还要自赖东泽十九岁说起。
赖东泽十九岁从台南到台北上大学,有阵子过得很忧郁,逐渐「发现」自已的脑子里出现哑铃形状的公寓,还会伴随鬼压床。当他睁开眼睛,就会进入那个空间,穿过一道走廊,两边各有房间,有窗,没有出口。空间里有一个老人,背对走道坐在摇椅上,穿著白色唐装,后脑勺绑著辫子。在赖东泽状况最糟的时候,老人甚至出现在他的真实生活。
「那时在租屋处,屋内漆黑,我开著桌灯。老人不会碰我,但会数落我。我后来跑去当兵,打靶时,开枪的声音让我不舒服,老人的声音就出现了。他会对我说:『不然这样好了,等一下你上去,你就开枪自杀,你觉得怎么样?』后来我把子弹打完,老人就对我说:『你没有自杀,看来你还ok。』」
脑中的老人于今安在乎?赖东泽答道:「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甚且,他自有一套分辨幻觉与现实的方法──「如果脱掉眼镜,视线模糊,眼前人却是清楚的,那他们就是幻觉。」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荒谬的世界里,这个方法很具逻辑。
真枪实弹的童年记忆
赖东泽热爱军事,爱写军火题材,还熟知枪枝厂牌与型号。这源自他的家庭背景──父亲是霹雳小组成员,母亲是刑警,见到真枪的机会比玩具枪还多。
赖东泽回忆,某次警察搜到很罕见的枪枝,开记者会展示时,得在每支枪前放上名牌,他便被母亲带去指认型号,看到有错,还纠正母亲:「这把不是九零手枪,这是比利时FN枪厂,枪款是FN57。」
赖东泽甚至能分析台湾枪支来源,一开口就源源不绝。「台湾的军火零售商就像鸡尾酒,进口大宗是菲律宾。八九零年代,越战刚结束,还有中越战争,很多越南人往外跑,跑到香港抢钱、抢银行,于是香港就有飞虎队、反恐行动。有一些人跑到台湾来,也从越南弄来很多枪。越南因为打过越战,又曾受中国和苏联资助,所以美系枪枝、俄系枪枝都有。这些最后都出现在台湾。」
藉由枪火,赖东泽得以拉出一条全球战争史,以及家族史,不大美好的那种。他曾在其他访问中提到,小时候常被父母打,藤条、拳头、过肩摔,肉身即沙包。六岁时,他离家出走,用藤条插包袱,走在凤梨田。虽然最后他还是回了家,但与家庭和解,要到他当兵以后。
打杀、血腥、战争、死灭在赖东泽的文字和人生中一再出现,但他说:「我不喜欢与人冲突。」因为吵架是没有效率的事,赖东泽说,「排除法律与道德限制,当我不想听对方的意见时,最有效率的作法,就是直接杀掉对方。因此,干嘛吵架浪费时间呢?」说到这里,我开始回想上述问题是否有他「不想听的」。
好在他继续补充:「但是人在世上,就必须遵守法律和道德限制。既然不能杀人,那就连吵架都不需要了。」这是赖泽东式《罪与罚》了。
背向死亡迎来新生
 Lobot技术开始普及,成为随身携带的网路心理诊疗平台,但新型态心理病毒,也悄然成形……
Lobot技术开始普及,成为随身携带的网路心理诊疗平台,但新型态心理病毒,也悄然成形……
《潜脑侦查科》里有各式死亡,既血腥又离奇,简直是以死亡作烟花的马戏团。关于死亡,赖东泽自有一套实践与辩证。小学六年级时,赖东泽就思考:「我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什么?」那些看起来快乐的人,为何决定离弃这个世界,自杀这件事让当时的赖东泽困惑。
或许是拥有过多的感知能力,痛苦对他而言,是可触摸的。赖东泽不讳言,他曾从五楼跳下来,结果压坏人家车棚,也试过割腕和手臂。「但我不鼓励自杀。」赖东泽强调。《潜脑侦查科》探求死者的地狱,新的电影剧本《红星孤旅》则为我们上演火星任务官的求生之旅。故事讲述一趟单程火星任务,成员仅有一名人类和他的机器伙伴,以及量子电脑构成的人工智慧。人工智慧渴望人类陪伴,甚至惩罚不陪伴「她」的人类。在绝对孤寂的火星上,唯二的智慧体竟不是相互取暖,而是各怀所思,想掌控与拒绝被掌控;寂寞与逃离,原是一体两面。
此外,是「她」没错。这是一个女性化的人工智慧。是否隐喻两性关系?就留待读者与作者各怀所思吧。
《红星孤旅》最后,主角漂流在太空中,落入绝对的孤绝,那是巨大又无声的痛苦。我想起《潜脑侦查科》的主角曾说:「痛苦是精神的养分。」赖东泽则用幻觉带来的苦痛,与生在苦痛中所诞生的文字为我们示范这句话。「那些过得安逸的历史人物,能创造出什么东西呢?」他以补刀的口吻继续说道。
不喜欢这个世界,所以透过剧本创造一个新的,这是他的写作企图。背对死亡,赖泽东迎向文字世界的诞生。「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死,才是制造浪费。所以我活著,非得创造点什么。」
所以赖东泽讨厌浪费食物。
他为我描述,试想:有一只猪必须活在狭窄的环境,成年后成为人类的食物,被宰杀,被支解。然后有人点了一份排骨饭──来自这只猪的躯体,必须切片、裹粉、油炸过。最后竟被嫌弃,岂可原谅?
我想起我浪费过的所有排骨饭,流下一阵冷汗──脑中浮现自己变成被人嫌弃的排骨饭。此刻,赖东泽成功在我脑海中描绘出属于他的地狱图。潜脑非关科技,而是赖东泽的超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