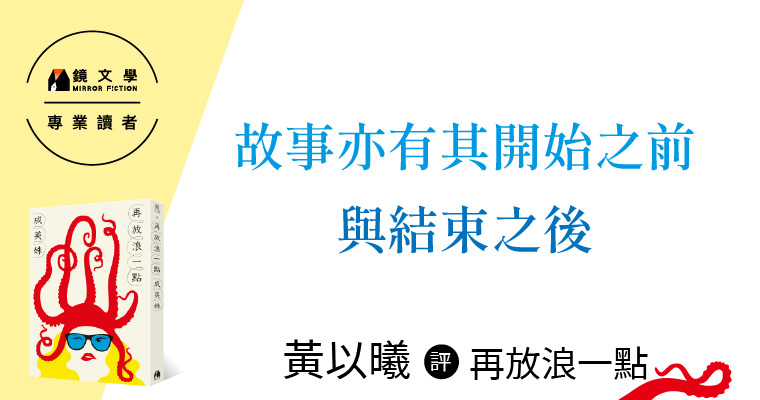
故事亦有其开始之前与结束之后——黄以曦评《再放浪一点》
成英姝的新作《再放浪一点》,是一本关于女人的“我”的小说。但什么是女人的“我”?当女人说“我”或“自己”,那指的是什么?得先有自己的房间吗?是除去性别底蕴、坚守“人”的纯粹内涵吗?在日常、在角色、在关系底,探问“我”,真是可能的吗?当人们说“多爱自己一点”,那是什么意思?或者,更令人费解的,“爱自己才能被爱”、“先爱自己才能爱他人”,又是什么?以及,“永远要保有自我”,那的需要被保有的是怎样的东西,且是由谁来保有?《再放浪一点》成英姝 著出版日期:2020/6/12什么是女人的“我”?在《再放浪一点》,有四个女人,一是书中的“我”,叫爱莫,三十六岁,卡在艺术与商业瓶颈的不得志编剧;一是年轻演员由果,长相和身材俱不尽符合演艺圈标准,发展不顺利,但乐天又努力;一是资深也已退役的演员龚丽莲,念著年轻的风光,找上爱莫为她量身打造剧本,期望再次东山再起;一是跑通告上节目的知名心理学家梁梦汝。爱莫和由果同租一处,龚丽莲为了剧本也跑来一起住,梁梦汝则是该共居生活中时不时出现的友人。表面上,《再放浪一点》是个非常冷淡的故事。这四个女人在都会浮沈,许多挫折、落寞,有几乎成为感动的快乐、更多时候则只是日子淡淡到来又离开。四个人生,故事似乎赋予其间的交集与牵动,但到底是错觉、错解,因为每处辐臻点,仍由每个人的生命轴线各自定义。换句话说,她们紧密且错综地交往相处,但每个生活都是独立的,甚至透有断然的气息。那非关拒绝,非关性格里的乖僻,而仅仅是,她们都拥有某个绝对性的自我,就算她们自己毫未察觉、也不曾由此去强调。四个人,可以有多少种排列组合,书里就有多少可供拆解细究的独立关系,爱莫+由果、爱莫+龚、龚+梁、由果+龚+梁爱莫+由果+龚+梁、……,在并无太多情节起伏转折底,通过整份叠图效应,每个人的轮廓渐渐显明、鲜明,到后来且像是某种执拗,成为了命运般的角色。我们看穿她们每个人是如何来到这一天,而在书页结束后,又将走向哪里。她们都是很平凡的人,这里说的平凡,指那些模板化的表现,即使是抗拒主流、忠于初衷、热爱或失望于生命,即使是不同于通常女性生命历程的毫未牵绊于丈夫、小孩、父母,她们仍是我们绝不陌生的样子:似是而非的人生反省、煞有介事的梦想追寻、关于爱与友谊的入戏唱和……。《再放浪一点》给出一个“自以为可以不世俗,可终究无法不为世俗吞噬”的场景,而在此一时刻,这些女人之于自我审视与评量的诚实,将揭晓,以一般性、共通性处境而言,我们的灵魂在这个世俗里还可能怎样穷尽?是否真有任何价值?别的编剧愿意遵循商业风向,写出叫座且也不一定不叫好的作品,爱莫无法是那样的人;别的女演员忙著医美瘦身以潜规则搏上位,由果不留后路地深潜入一个配角;别的退役演员默默让位,让往事成云烟,龚丽莲却不畏取笑要重新进驻;别的畅销作家拼代言上通告,梁梦汝却更浮沈于无止尽内心戏。是的,她们和多数人不同,但真又有那么特别吗?而到头来,假如特立独行、坚持自我,看起来也没有更帅、反而错过更好的待遇,这一切是否徒劳可笑?还是说,正是由这种不值、这种近乎可悲,反过来提示:叛逆是容易的、作自己是容易的,重点不在这里,而是,反正,面对这样的世界,人从来就输无可输?《再放浪一点》珍贵地勒令关于人生的自主与清明,可以是寻常而当然的选择,它不为了意识形态的演化或争夺,亦绝不保证感觉良好,它只是一个应该被直觉地、无条件地纳入考量的选项。故事里,这些女人或有可爱之处,但也跟其之不可爱,不相上下,成为一个“挂念自己是谁”的人,不为了变得可爱,但也非关不可爱。成英姝的作品里永远有种顽强的虚无,那不是厌世、不是对(反)价值的捍卫、不是“看透”、亦不是“何必看透”,而是一种对于当下、对于此在的执著。怀抱如此执著,之于流转的时间与人世,必然脱落。《再放浪一点》亦贯穿著从那样的由彼个无法成立于任何哪里的视角,对生命的遥遥凝望。小说中有一部爱莫为龚丽莲写的剧本,小说家这样写女主角S,“S有一种超乎常人的神经质,以及各种矛盾,她既敏锐又粗率,她在莫名其妙的地方执拗,普通人都知道该遵守的法则毫不在乎。她的问题很多,却无视于关键的答案,她喜欢装作老于世故,他却觉得她一派天真。她发现自己在学新的事物,……学著当一个新的人,……她觉得自己就像电影里的人物。……现在她的生活里没有别人,没人会提醒她过去这一生的线索,她丝毫不想那些。”不意外,但依然惊悚的是,这部戏中戏里的女主角,或可看为是在将小说中这些女人浮荡又闪烁的状态给重新锚定。她们都是S,她们是电影里的人物,而这是四部分别开来的电影,我们读到的一个屋檐下貌似女性情谊的种种,终究只是幢幢幻影。那部戏中戏像个玩笑或狂想地毫不合理,又任性或挑衅地关闭。它在小说的中间,某意义而言,《再放浪一点》的都会女性自觉旅程,在终点到来之前,早已公布结局:怎样戏剧化的人生、潮浪起伏的际遇,都虚假单薄,像个布景,你配合演了一路,在里面获得一些真实,分享一些真实,但你无法在那里。你是空的。只是,尽管是空的,那些流动的夜晚仍是美的。这份美,是不可能否认的真实,至于那是否让走一切变得值得,不必是同一回事。女人是双层的、多层的。如何标记女人的自我?那是统御著增生繁错的无数自我的更后面、更高的那个“我”。是以,她无法不是透明而淡漠的。《再放浪一点》中的女人,每个都说了很多话,争相表达辩论著心思,但其实那都不是她们的“我”;真正的她们的“我”,漂荡在半空,无可无不可地看著自己说话。那每个女人,越是执著深入就越疏离,越是亲昵就越冷眼与寂寞。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成立:她们独自时仍那么温暖、充满关怀,她们和彼此赌气斗心机,越是激烈,就有越多“一起孤单”的感激、包容与爱。《再放浪一点》说,人们一生就像在说一个故事,但这故事又包含著无数个小的故事。故事换了方式去看、去说,就成了一个故事,那么,“故事究竟有没有它自己?”、“那个它自己又是什么、在什么时刻诞生的?”小说家与人物齐声追索。这或者是个文学的提问,但它亦是个存在的提问。当大故事包含著小故事,并非小故事组合成了大故事,而是,当大故事勾勒边界和朝向、牵制小故事的生成与挤压、小故事争竞与求存、而那或者未能改变大故事的类型和格局、却在里头深植了类似情感、价值、幻影与真实的东西。那么,我们还如何正确“看到”这个故事:“它”是小故事的聚散平衡,还是大故事的始终俨然?《再放浪一点》里是数个女人的大故事吗?那些小故事真参与塑形她们各自最后的样子吗?而这些女人各自的人生、以及一部部的戏中戏,又在连动地使那一个终极的大故事浮现?而当换置了故事自己的视角,则“我”是变得悬缺而可疑吗?还是这才是“我”的样子:清明的距离,却有肉身无止地牵扯忙碌,由此在不可测的命运彼边,织就整个对反的模样,是为“我”?本文作者黄以曦,作家,影评人,著有《离席:为什么看电影?》《谜样场景:自我戏剧的迷宫》《尤里西斯的狗》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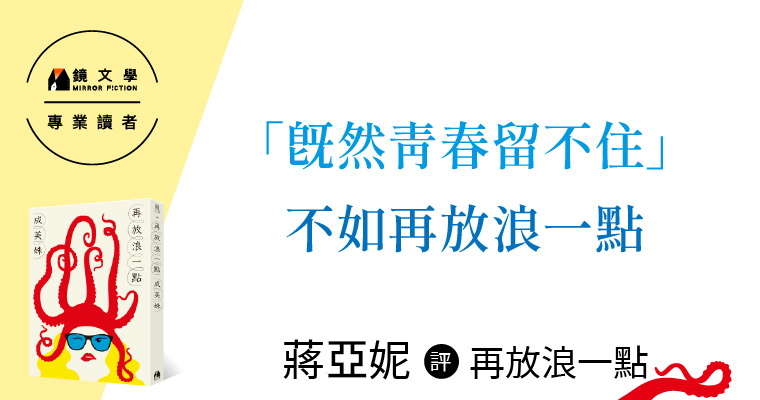
“既然青春留不住”,不如再放浪一点——蒋亞妮读成英姝《再放浪一点》
我很害怕单一化。不管是一件事、一种称呼、一个版块或一类性别,比如“女性文学”、“女性作家”与“女性书写”(替换成同志亦然),但我明白这些存在,依然有其必要性,因为世界确不存在专指男性书写的“男性文学”,我们只能不断催熟“其他”、壮大“之外”。成英姝的最新长篇《再放浪一点》,距前作《寂光与烈焰》整整四年,男赛车手开出记忆的荒漠,这次的小说主角是三个有欲望、有野心的女性。成英姝只使用了一个进行中的“剧本”,便将三者串连。三十多岁的女编剧高爱莫,一直期待写出畅销剧本,却总是心比手高;五十多岁的过气艳星巩丽莲,将最后翻红的机会压在请高爱莫为她打造的剧本上;最后是二十多岁的Z咖女演员林由果,为了演出机会极尽卖傻、卖疯、卖性感,抛售羞耻。不经意处,有著张艾嘉2004年电影《20.30.40》的女性年龄思考,或许一点1994年王晶电影盛世时期《恋爱的天空》(又作《四个好色的女人》)中的自觉与讥诮,偶尔闪过2013年黄真真执导的《闺蜜》里,少数精彩大胆的生动对白,叠影混搭。说穿了,《再放浪一点》是讲女性的小说,却不该被单一化为女性小说,这是我深以为戒的阅读整理。1990年“布克奖”得主,英国作家A.S.拜厄特说过:“如果要做为一个好的女作家,你首先要是一个好的作家,而不是仅仅和女作家在一起,大家只讨论女性的事情。”这与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说过的:“在这个世上,我首先得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放在一起看,相当有趣。事情的优先顺序永远是,先是一个怎样的人、才是一个怎样的作家,至于性别,万万不需要沦落为少数族群与偏远地区一般的加分要点。成英姝虽然在《再放浪一点》不断拿针戳出女性的血点,像是谈到年纪时,她写四十多岁女人的屁股,会从短裤下缘垂出,但穿的却不是热裤;可四十多岁也不全然缺点,比如女人拉皮:“都说拉皮就要趁年轻,大概四十多岁最好,拉了能定型,还好看,老了才做,三两下就崩坏了。”幽默的最高级是开自己玩笑,这点成英姝与她小说中的三个女人都做到了(换成男性处理就容易落得政治不正确)。如果就只停留在此,三个女人一台戏,就算再加上一个畅销名作家梁梦汝与时尚设计师维若妮卡,五个女人大搞女性主义,唱得也还是过于单调了。还好,成英姝不需要女性加分,她在《男妲》跟《地狱门》等长篇作品里,已经自证这点。不管是暴力、类型、情色与异色,她都玩过了,所以我们必须看进深处,穿越性别、翻玩意识。大家应该都听闻过维吉尼亚·吴尔芙那如当代夏娃宣言般的“自己的房间”,女性(尤其写作者)要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房间需能上锁。不过吴尔芙的原句不只这些,而是:“女性要想写小说或诗歌,必须有五百镑年金和一间带锁的房间。”散文集《自己的房间》出版于1930年前后的英国,作个简单计算,那时的500英镑约等于如今的120万至150万新台币(相近当时英国中产阶级以上男性年收入)。吴尔芙与她“500英镑说”也非凭空发论,刚好是她姑妈留予她的遗产年金。可惜,根据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民国107至108年平均年收入,当代台湾女性大约落在57万至60万间,小说中的三个主角大约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当我们都少有“500英镑”年收时,就不再写了吗?答案很简单,不管你是男是女、优渥还是落魄,都得要写。反正生活再惨,小说里得暂时靠海苔片、泡面、豆腐撑过生活的女编剧也宽慰自苦地说了:“几个月接不到工作,明明过著清贫的生活,却一点也没瘦,又是一桩宇宙并非逻辑建构的证明。”编剧也好、作家也好、画家编辑老师都是,拿著笔的一个都逃不了,比起性别,《再放浪一点》的主体,更靠近一群无处可归、无路可出的现代人。这不禁让我想到多年前成英姝在“三少四壮集”发表的短文〈我们都太在意永远〉,她写喜欢的作家:“托尔金的世界是一个放置在真实的凡俗的平淡无奇的世界中的箱子,两者平行重叠,当浓雾遮盖了视线,有时拨开那白色的帘幕,就会置身在托尔金的世界中。有一种电影情节,主角意外或者为了某种目的,来到了另一个时空,大部分的剧情,最后都让他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这也是我在读这本小说的感受,当我在小说世界、他者时空,游历一场后,却发现听到的全是我自己世界的回音与困境。比如,故事的存在可能;比如,美好的总是往日时光。虽然美国小说家劳伦斯·卜洛克声明:“伪造正是小说的核心与灵魂。”而在一众台湾小说家中,成英姝很高程度地展演了她虚构(Fiction)的能力,私小说的座位,即使你拿著她生平门票一幕幕寻找,最多也只能看见经过了离解、脱墨、洗涤、漂白而还魂的再生纸,前人的名字与笔迹,你找不到。她是罕有地认真说故事的人,为我们展演她精心设计的一个又一个“灵晕”(aura)。灵晕就像故事的入场卷,你得透过它才能真正进入故事氛围。她通过小说中编剧角色的困局,狠狠敲击了当代文学一直讨论不休的:该怎么说故事、还有没有故事,以及有没有人还在说故事?于是在小说故事完结前,她忽然花了许多段落定义“故事”:“故事究竟有没有它自己?那个它自己又是什么,在什么时刻诞生的?人的一生说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无穷的故事散乱,充满矛盾、歧义,它们会被什么指向一处,变成同一个故事吗?⋯⋯事实上,每个故事在当下便已完成了,每一个瞬间就涵盖了过去和未来的可能,在那个点上,它已经是完整的了,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成英姝以故事作答故事存在,故事是有可能的,小说依然在说著不同故事与包裹故事,故事里又再藏著些许内在自我。小说随著主线“剧本”的完成,走向结尾,最聪明者显得蠢笨、最痴傻者却看得最清,撕逼的人说不定相知相惜,这样的安排在小说里并不特别,特别之处是成英姝洞悉世情的口吻,当她写道别人教训爱莫的编剧态度时,说的是:“你犯的这个毛病也反映在你的创作态度里,你鄙视陈腔滥调,你对于无论是别人或者自己曾经说过的话都认为没有价值重复,但你以为真理有多少?”过去了,才有来处可以回头,天真过,也才能说世故的语言。我和小说同时惊觉,现在的所有故事,都由“过往”触发至今,就像五十多岁的昔日艳星高谈自己仍有粉红色乳头一样,看似放浪的全是幻梦。每一个小说的角色都困于旧日,尚未发福的身材也好、捧在手心的爱或是充满可能的未来都结束了,于是小说为他们写下:“以为永远记住我们年轻时的样子,仿佛就能回到过去,但过去就和未来一样,从不在默默那里等待。”说的其实是,往日时光,早已远去。“回不去”的不只叫半生缘,方文山为南拳妈妈写的歌里,那年Lara也唱著:“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也都无家乡、无归途。既然无家无乡(也没有吴尔芙说的百万年金)、既然青春终究留不住(也活不成李宗盛一样的成功大叔),成英姝告诉我们,不如再放浪一点,反正,没有从前了。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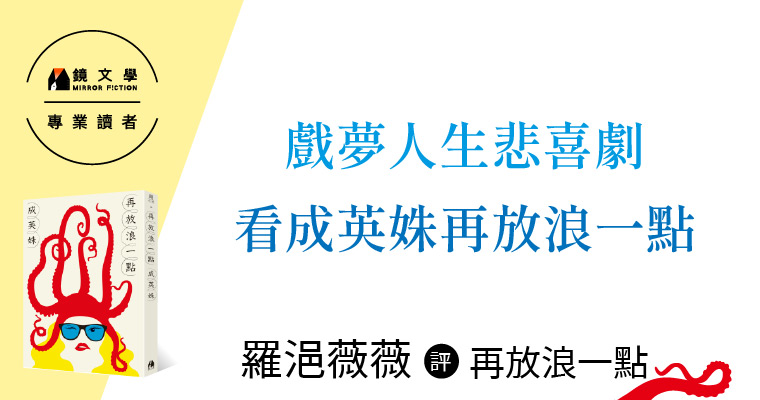
戏梦人生悲喜剧——罗浥薇薇看成英姝《再放浪一点》
我有一群不三不四的朋友,在脸书上开了个名为「D级俱乐部」的私人群组,里头有大学教授、家庭主妇、烘豆师、海外游子、动画师、无业游民、艺术家等等共计十一人。这是个第一时间很难令人理解的神秘组合,但里头或积极或潜水、身怀各自武功门派的成员,加上版面里每日的插科打诨与世界奇闻转帖,让这俱乐部从一开始的无心插柳到而今的藤漫成墙,人人皆从自甘低级的嘲讽底下寻出最小众的乐子,并深深相信彼此必定能理解其中暗语。《再放浪一点》成英姝 着出版日期:2020/6/12看了《再放浪一点》,我一直在想自己的D级俱乐部,认真思索着此类秘密结社之必要。说秘密,其实这并非一开始便得说出口的要件(毕竟说得出口的就不叫做秘密了),而是一种气味,加上(听起来无比老套的)缘分。于是我们得到了爱莫、梁梦汝、巩丽莲、由果,四个阴错阳差、既排拒又亲昵的角色,成英姝描摹人物,尤其女性,真是一绝,相较起她眼底各形各色环肥燕瘦的都会女子,所有的男性都成了配角。她擅于运用活灵活现的人物及情节带动故事的节奏感,那些对话尤其简练精彩,你完全可以想象它被改编成舞台剧:「我小时候好向往院子有游泳池的房子,我心想,得多有钱的人家才拥有游泳池啊?」由果说。「人总是会向往没有用的东西,要游泳池到运动中心就好了,买月票才1500,不限次数。你知道养一个游泳池要花多少钱?还没有跑车实际。」巩丽莲说。「你都到公立运动中心游泳?」我问。「当然不!我是女明星,给人认出来怎么是好?」巩丽莲说。「她都去那种养生游泳池,有三温暖和草药浴的,草药池里头还放姜,老人都去那儿。」梁梦汝说。由果的天真烂漫、爱莫的追问者性格、巩丽莲与梁梦汝的看来互相吐槽实则交心至深,四个人从面部表情到人生观,在这个场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之中便生动描摹出来。成英姝笔下的都会女性,所需面对最波涛汹涌的,已并非社会架构底下的客观性别困境,更多是直面规范之后自我与他者的对话,而这个「自我」与「他者」在《再放浪一点》里,实为一体两面、无法分割。爱莫在看待与书写身边各色女子的同时,看似客观辛辣自有想法,但深究之后我们会发觉,所有的想法之中都包含着她对自身、人际、乃至于整个社会的的主观想象。作为一个说故事的人,如同《伤心咖啡店之歌》里头的马蒂,成英姝在故事里藉主角的呓语,像在镜子屋那样抚着镜中的自己,一面自问自答、苦于毫无出路,一面仍舍弃不了内心深处对于(尽管可能永远走不到的)洞穴尽头那丝光亮的一抹想象:「人的一生说了数不清的故事,这些无穷的故事散乱,充满矛盾、歧义,它们会被什么指向一处,变成同一个故事呢?」「……,但事实上,每个故事在当下便已完成了,每一个瞬间就涵盖了过去和未来的可能,在那个点上,它已经是完整的了,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人或可以眷恋、频频回首、踌躇未知,但活着这件事只发生、结束在当下片刻,不仰赖倒带或者不确定的未来,因为它自己就是过去与未来。」四个个性迥异的女人们在铺陈了大半篇章后,终于抛开俗世种种、真正地乘着喷射机离去,在旖旎南国共处一室。你若曾经计划这样的旅行过,便能理解最理想的旅伴不是爱人,也不好是与你太过相似的人,这有点难解释,大致就像小说里四位女主角那样,可以疯癫可以拌嘴可以完全接住你,但绝不轻易把「包容」说出口。在异乡的放大镜之下,你会发现自己的开放性与想象力都水涨船高,角色性格与故事走向至此渐渐收拢而愈见清晰,那就算快被现实磨损殆尽也难全然舍弃的温柔慈悲由此淡淡浮现。我是从晓天与晴恩的支线看见那温柔的。相较起小说中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对话,这段故事几乎可说是既唯心而又梦幻。我不愿说那是一段架空的情节,我还愿意相信人们生命中都拥有一个晓天或者晴恩,又或者我们都当过那个只愿享受他人全心的爱却付出无能的爱莫,我甚至为心有不甘的骄傲的她感觉不舍,都已身在那最后时刻,明明无关爱与不爱,还是不愿在情感棋局上弃子:「我不愿意让晴恩知道晓天忘记我了,这是一种耻辱,我不想在晴恩面前认输,但事实上,在晓天和晴恩之间,我已经不存在。」那是一个意欲证明自己「切实存在」的象征,透过他人错认晓天的爱的投向,稳固了爱莫的重量,尽管她如此理解那最初的、「属于她的」一切皆不再,「失忆」的现实与象征性,恰恰铺陈了这故事中为晴恩量身订作的,也是整本小说中最诗意喟叹、也最接近梦境的时刻。那也是整本书几乎唯一以怀柔方式坦白出爱莫(我们)自以为与众不同、实则害怕就这样遭记忆(时代/年龄)淹没的无声恐惧。而她清楚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对所有人而言,没有所谓的救赎,也没有Happy Ending,唯有坦然地(即使一开始是装出来地)大步向前迈,才有机会一再变换/坚持「自己的」样子。没法抵挡命运的嘲弄,至少走也走得看来无畏洒脱。《再放浪一点》原本有个简洁些、不过确实有点过分话中有话的前书名,我并不确定是作者或是编辑的意思让《再放浪一点》最末出线,但在读过原稿几次之后,我忽然能够感受到在那些灯红酒绿却又相濡以沫的迟暮老派之爱背后,如此看透世情的心有不甘,这让「再放浪一点」几个字的积极与活泼完整地妆点了这无名俱乐部的午夜时分。旅行归来,说故事的人爱莫以自己进行得不甚顺利的剧中剧为引,铺陈了读者的悲喜情绪也同时暗示了接下来的情节走向。于是我们跟着她们一齐走到了看似荒谬而又萦绕淡淡哀愁的戏剧性转折点。在看似戛然而止的故事末端,爱莫这样跟巩丽莲说了一句话,大抵总和了这个大龄女子俱乐部的主题:「我觉得梁梦汝会比较希望我们笑,而不是哭。」散场过后,红绒布幕再次拉开,舞台聚光灯打在主角身上。人生如戏,戏若人生,有时欢天喜地、有时悲伤不能自已。趁灯光还昏暗,女子们便落下那只歪坏的长颈鹿,笑着向未来(过往)跑去。
+ Mor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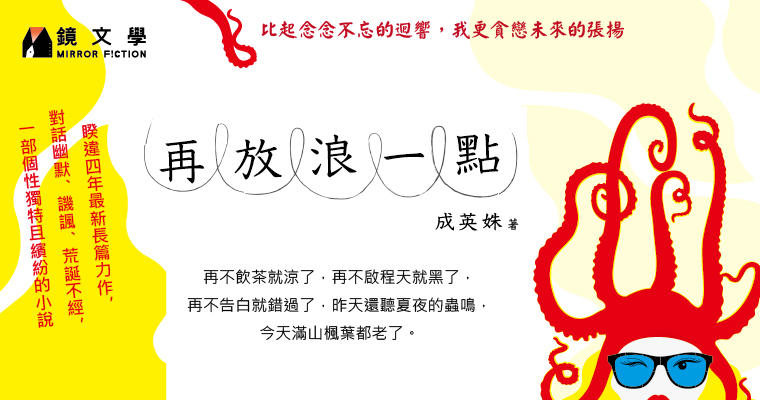
【镜文学出版】再放浪一点
《再放浪一点》成英姝 著出版日期:2020/6/12★睽违四年最新长篇力作,对话幽默、讥讽、荒诞不经,一部个性独特且缤纷的小说。──人生演到这,明明觉得自己是明星体质却老是在跑龙套?──如果你因为《公主彻夜未眠》知道成英姝,你会因为这一本更贴近她,以及你自己。中年之后,成英姝以幽默直视人生的荒诞与缺口,笔锋再次绽放,将我们的人生写成一场喜剧。---------过气女星巩丽莲,找上了自认怀才不遇的编剧高爱莫,拉著行李闯进爱莫与室友C咖演员林由果的生活,要爱莫为她量身打造剧本,从此个性南辕北辙的三人共居一室──接下工作的爱莫,剧本总被说只有自己看得懂,却抱怨起巩丽莲的过往无趣,而巩丽莲在意的却只有床戏跟吻戏;林由果则用尽心思搏上位,希望能争取在大导演的片中担任配角。就在林由果电影杀青之后,巩丽莲提议三人共游泰国,爱莫认定巩丽莲将不久于世,才急著留下代表作,而林由果仍然玩世疯狂,却不知即将迎接人生最戏剧性的转变……随著越趋疯狂的旅程,爱莫为巩丽莲撰写的剧本也随之越来越清晰。三人的人生剧本,最终走到转折点──可能将她们往人生高处推去,或是往人生谷底推落……再不饮茶就凉了,再不启程天就黑了,再不告白就错过了,昨天还听夏夜的虫鸣,今天满山枫叶都老了。作者简介成英姝一转眼写了二十几年的小说,世界是莫比斯环,一路直直走,正面都成了反面,黑成了白,左成了右,看著烟火灿烂,看著烟火熄灭,听筵席的喧嚣,送离人散去,没有回响的念念不忘,无人站在灯火阑珊,生命是阴差阳错,北极最后一块冰层破了,科学家预测再五十年人类走向灭亡,人生在世只有当下是真。今年的愿望吹牛不打草稿,微老不尊,立地成魔。著有《公主彻夜未眠》、《寂光与烈焰》等。
+ More
成英姝谈新小说—因为死亡很近,所以要《再放浪一点》
如果写作是作者用笔努力抓住世界,生命的吉光片羽——童年尝过的玛德莲,女人在台灯下如米色蛾翅的睫毛,那场落在全都柏林与死者身上的雪。成英姝写《再放浪一点》,却开始「放掉」了。「以前写作于我是那里有好美的极光,我也想让你瞧瞧,现在我会想你没看见,关我什么事?」一身长版宽T恤,扎起黄褐色头发的成英姝说。我想写活得理直气壮的女性是退化吗?毋宁是更自在的境界。只是这自在求不得,而是哀乐中年后的自救之道。成英姝1994年出版《公主彻夜未眠》,在荒谬见人生的悲哀真章,1998年《好女孩不做》写乖顺背后的冷酷异境,2000年写推理小说《无伴奏安魂曲》却也反推理,杀戮变得虚无,寂寞才是酿罪。凡此种种与以降之作,都带有手术刀般的锐利直取。这一回她写《再放浪一点》,三个不同年纪身处娱乐圈的女性故事,有编剧、新兴演员、过气演员,都在娱乐圈外围,努力靠近核心。有人成功了,有人放手,有人死了。听起来一点都不逐梦励志,成英姝说,「为何人们都想变得越多人知道越好,觉得这就是成功?我只是想写有生命力的女人,她们活着,且活得理直气壮。」所以失败不是失败,是你活过的未境之路。好女孩不做也没关系,风风火火一回就够。这也是成英姝的人生哲学,「现在写东西我自问:『我想证明什么?』或许是写的片刻我有没有努力做到活着的感觉,角色活着我就活着。所以写小说我注重畅快感,甚至不觉得小说是虚构的。」我们习惯看到青春正盛的男女主角在三幕剧结构中受挫、成长,但《再放浪一点》反过来聚焦若有所失的中年后女性——「现在」好像没有不好,然而再往前, 会触底还是升华?人生最难,便是难在不知该向前还是原地解散。没有一番成就,没有婚姻倚靠,女性该何去何从?成英姝敏锐捕捉这些感觉人生有点不对劲的女性,浮沉在自我与外物之间的险象。▲成英姝很早便因小说《公主彻夜未眠》闻名,被冠以天才作家、黑色幽默女王等名号。写作多年,她说写小说的过程就像在小说里活一遭,上一本《寂光与烈焰》写了五年,「简直像在里面住了一辈子。」《再放浪一点》虽仅花半年写完,但背后是她近年对人生的想法转折。(图/镜文学)不证明你自己,你就不存在《再放浪一点》三位主角中,「爱莫」是编剧,创造角色;她的室友「由果」是小演员,诠释角色;爱莫的雇主——过气女明星「巩丽莲」——则希望重新获得角色。换上面具,扮演「角色」在小说里变成一种渴望,驱使她们向前。成英姝说,「如果你不证明自己的存在,你就不存在。所以我的角色都是很自我中心的人。」除了自我中心,她笔下角色也几乎是不传统的女性,公主可以彻夜未眠,女流之辈似魔术也像奇花,「有时我也觉得奇怪,为何我笔下人物都无法好好谈恋爱,结婚生子,当一个合格的妻子或母亲,总是对抗传统价值观。但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就是没有这样的经验,也无法想象跟别人建立家庭。」成英姝善写兼具刁钻与美的女人,所以《再放浪一点》同样有不甘平淡的女性,「我没有刻意展现某种价值观,对我来说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就是写不出别种样子。」没有别种样子,就是成英姝。她说,「作家找寻自己的语言,是为了什么?为了美学?不是,是找出你自己的角度。找出原来这就是『我』。你怎么写就是你怎么活。」采访到一半,成英姝点的拿铁来了,便说好漂亮要拍张照。于是她开始选角度,摆姿势,谈摄影。「拍东西也让我感到视角的重要,每个人看事物都是跟别人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摄影对我来说就是展现『我怎么看』。拍食物很寻常,可是一桌的人每个人都拍得不一样。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每个时刻你用自己的视角看每个东西,串连起来,就这样过了一生。」小说写二十、三十、五十的女性,有的敢冲敢撞,有的裹足不前,还有铅华洗尽,却重新照见自我的,都是成英姝怎么活的证明,「常有人问我某角色是不是我的写照,其实整本书都是我,都是我站在她们的视角想出的,都是我的一部分。」因此,《再放浪一点》带着成英姝专属的洒脱。纵使写娱乐圈,《再放浪一点》不纸醉金迷,而是透过女性在这由男性凝视建构的场域衬托其虚伪。小说几位女主角最放飞自我的时刻,则让人想起珍・芳达演的《同妻俱乐部》,笑闹间,人生熙熙攘攘、兵马倥偬都可以是姐妹的下午茶时光。▲拿铁上桌,成英姝乔角度拍照。她兴趣广泛,从摄影到灵修甚至赛车,自言一直以来都对次文化潮流很有兴趣,「因为次文化潮流是生命力的展现,有最多最新鲜的热情。」(图/镜文学)死亡在前,你要留下什么?《再放浪一点》其中一条主线是巩丽莲请爱莫为她量身打造剧本,因为可能命不久矣。生命花火最终,谁都想再亮一回。因此,小说无可免的触碰死亡议题,但读者可能会跟着笑。现实中,成英姝接连遭遇亲友过世,一开始是养了多年的狗,隔一个月后她父亲过世,两年后她妹妹在她出国时动手术,两个星期后也走了。最近她又送走交往二十年的男友。疫情期间,时不时传来她对岸朋友突如其来失去身边亲人,「生命竟就是如此轻易无声无息灰飞烟灭。」「现在我已经做好准备随时会走。时时刻刻我都在想,人生说走就走,我留下了什么?每天都在找答案,但找不到。」死亡已被预知,成英姝说那就活在当下吧,「但我发现活在当下不是把握什么,而是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这些都不想。我的过去与现在无关,而我的当下也不影响我的未来,因为我连明天有没有都不知道。」话虽如此,成英姝说死前还是有一定要做的事:删掉计算机里的草稿跟未完成作品。作品不重要了吗?成英姝说,「没了就没了吧。」好像中年以后人生就是不断的救死扶伤,直到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听起来中年后就是一路下坡,但成英姝用喜剧面向死亡,她说写《再放浪一点》写到她自己都会笑。▲她第一个刺青是十年前刺的。本来不知道刺啥,但有一天想开,就果断去刺了。会不会后悔刺青图案?成英姝说,「会啊,人生就是一定会后悔,但谁在乎呢?人生不就这样吗?想法一定会改变。人生如果没有改变,多可怕?」(图/镜文学)努力在现世与虚拟获得补偿《再放浪一点》最浪最好笑的是女人间的唇枪舌战。成英姝爱写对话,尤其是麻利的对话,「我喜欢表达人,要强调一个人的个性,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她的语言。」同时她爱讲话,小学没什么朋友,上课却总是跟坐旁边的同学发表自己的见地,「那人甚至不是我朋友,我只是想说话。」以前跟作家友人动辄在咖啡馆聊七八个小时也不会累。听起来成英姝很需要热闹,可是她又享受绝对的自由与孤独,想到再谈恋爱,心中会牵绊他人,就让她打退堂鼓,「所以一个人过活就好。」看似潇洒,连作品都不在乎,但成英姝还是有生活之必须——宝可梦。难道不写作时都在抓宝吗?成英姝说,「写作和抓宝并不冲突。事实上,游戏跟人生一样是虚拟的,虚拟的程度没有不同。」然而,成英姝其实有段时间没玩,重新迷上宝可梦是在她男友丧礼上,遇见二十多年来几乎没联络的男友姐姐。等火化时,成英姝发现他姐姐在抓宝,于是也跟着抓。对方还教她新出的团体战要怎么打。听起来像卡缪《异乡人》里的情节,只是没有人被抓去审判。女主角爱莫在里头说:「我认为戏剧的诞生,来自一种补偿作用,对现实、真实生活的补偿。」成英姝说写小说也是这样,「我觉得这是我可以一直写下去的原因。」所以现世里有很多遗恨吗?要用小说给自己一个交代。就像她手臂上的刺青,也是给自己的交代——当初是为了证明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有你没有才刺的,「现在我发现其实我跟别人本来就不一样啊。」「不过至少死在哪里时,别人马上就知道是我的尸体。」成英姝摸着手腕上象征灵性的蛇图腾说。也似抚起发痒的伤口。《再放浪一点》新书上市博客来:https://reurl.cc/MvLbXp诚品:https://reurl.cc/ZOqrXW金石堂:https://reurl.cc/4Rv4QD读册:https://reurl.cc/NjLpqk
+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