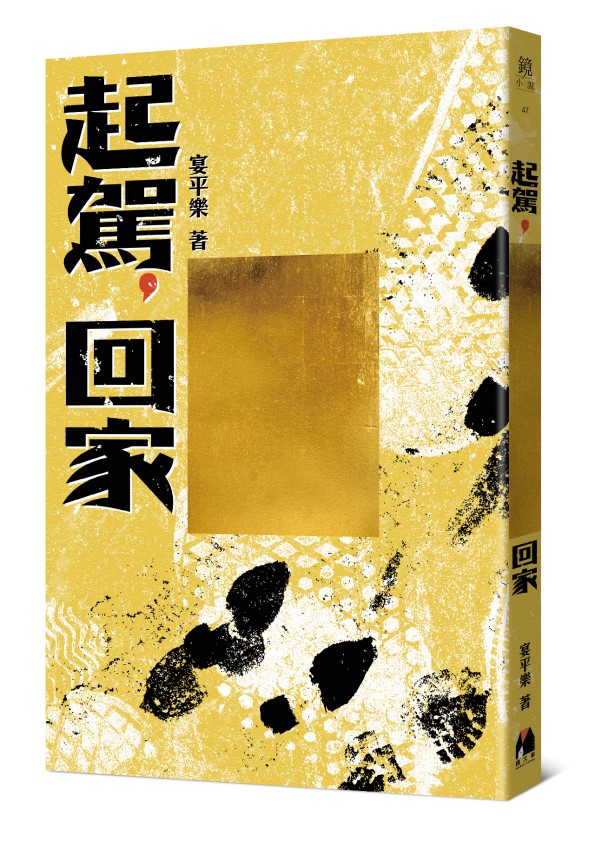我们在路上相会——宴平乐谈《起驾,回家》
文|翟翱
2021-08-10
去年六月,宴平乐第九次走完大甲妈祖绕境,并将这些年的经验写为小说《起驾,回家》。起驾是出发,回家则是为了再出发。参加九天八夜的绕境,耗尽体力又得餐风露宿。有志者如他,年复一年参加,想必有很强烈的动机吧?
然而宴平乐说,“每年都没特别为什么而走,还能走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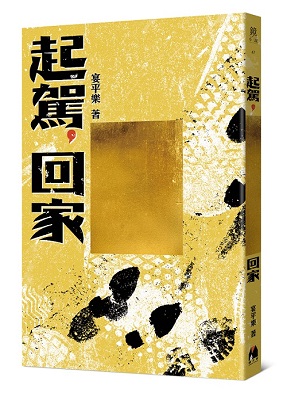
《起驾,回家》
宴平乐 著
出版日期:2021/7/30
融合绕境与浪子的故事
宴平乐国中开始创作,之前多写奇幻武侠。《起驾,回家》是现实中的现实题材,不但以大甲妈祖绕境为背景,更融合小时候回台中海线外婆家的经历——海线人靠捕鱼为生,每次出海都是拼搏,正如小说开篇写的“一个浪头打来,说翻就翻,早上出门,下午可能就回不了家的鱼寮。”
海的丰饶与无情,让宴平乐体会到生命的冲突与讽刺,“小时候我常听长辈用台语说‘谁谁流走了’,表示在海上出事了。海不会管你是好人坏人或老弱妇孺,流走就是流走了。习以为常后,死亡就变成很淡的哀伤,再来是无奈。长大后我发现靠海生活的人,生命很有韧性,可是生命又很不值钱。”
大海,也像酷刑,“老一辈不爱吃牡蛎,因为小时候他们都要赤手挖,伤口遇到海水会很痛。牡蛎对他们而言,不是美味,而是鲜血的记忆。”宴平乐谈起海,像遥远而沉淀的回忆。
生长于此的人们不免受其影响。生命的意义在凶险的环境里,不是与天逞凶斗狠,就是看透生死,变得很轻很轻,“出海跟拿枪一样危险,反过来说,一船回来也像干一票大的,要发家致富,”也就不难想像为何海线不缺道上兄弟。这成为《起驾,回家》连结绕境与浪子的原因。
《起驾,回家》讲述一对好友陈肇仁、蔡正国,一个为还愿一个要跑路,走上大甲妈绕境,一路上是鬼使神差的际遇,也是江湖恩怨的缩影。在路上,终究要告别,此后陈肇仁与蔡正国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如同现实中人们走绕境,“尽管路是一样的,每个人上路的方式却不同。”
因此,这是关于回家的故事,也是无法回家的故事。
“我看到很多人浪子回头,但也有很多人不想回头,认为自己走的是成功之道。这之间的冲突很有趣,因为妈祖是稳定人的力量,但兄弟拜的是关公;海线出生的他们,原生家庭拜妈祖,长大后自己改拜关公。然而在江湖闯荡,回到家还是想追求安定,重新拜起妈祖婆。”落实在小说,便是一开始陈肇仁、蔡正国在关公面前结拜。
绕境改变对生命的看法
小说中血气少年的江湖壮游看似要展开,实则却是走向自省的旅程。这点跟宴平乐开始走绕境的转变有关,“以前我对陌生人比较冷漠,走妈祖绕境后,理解到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跟意义,开始比较认真看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他对死亡的态度,也有了不同,“小时候死亡很日常,是淡淡的,走妈祖后才发觉生命有它的重量,开始觉得为何人命就这样没了?一样是生命,为何有的人要与海争?”
走绕境如何改变宴平乐?他表示,第一年完全没准备,走得很痛苦,烧裆(跨下内侧皮肤互相摩擦,引起皮肤肿痛甚至破皮)、脚起水泡都遇上,“我爸请一位72岁走了29年的老先生带我走,我看著他的背影一直走,只感到痛苦,没有其他。完成后,我就想是我能力不足,所以没能感受到别的。第二年我做了体能训练,才有馀力体会路上风景跟人情味。走了两年后,前辈就建议走完三年,无三不成礼。”
于今已走完三个三年,宴平乐也从菜鸟阶段有了些许心得,一路上的种种奇遇,让他相信力量是人走出来的。“有一年我走到龙井还大肚,已经半夜两点多,天气很冷。想到庙睡觉,结果挤满人。正当我摸摸鼻子走出来,忽然一个大叔跑向我——打扮像农夫,仿佛刚从田里走出来——塞了两颗地瓜给我。很神奇,他没有要给别人,而是直接锁定我。后来我边走边吃边哭。”

最难熬的一次,是宴平乐感冒。“即使天气冷,因为一直走会流很多汗,我走到吴厝时没注意体温掉太快,不小心感冒了。头晕到天摇地晃,走著走著,看到一个大姐远远走过来,手中拿著一杯姜茶,递给我说‘喝一点会比较好。’我就沿路喝姜茶,走到了新港奉天宫。”
“路上总会有人在你不行时推你一把。”宴平乐说。“参加绕境前要先‘起马’,掷筊问妈祖能不能让你加入,圣杯的话,只要你自己不放弃,妈祖会派天兵天将保佑你走完。”在《起驾,回家》里,这成为主角得以遇到天外救星的机关。“你可以选择相信是遇到贵人,也可以相信是妈祖显灵,前提是你想继续走下去,自助才可能天助。”
之后宴平乐走绕境,看到有人走路姿势怪怪的,疑似烧裆或起水泡,都会主动帮忙,例如向烧裆的人递上免洗三角裤,“很多人不好意思接受帮助,我们就说没关系你收著,给它一次机会试试看。”或许信仰并非形而上的东西,走完这条路的力量,就是信仰;在不知不觉之间,成为他人的天兵天将。
有趣的是,宴平乐的父亲是民俗摄影师,颇有名气。然而,以前他只觉得这个拿著相机追绕境、烧王船、炸寒单、蜂炮的爸爸,常常不在家,不过是回家时带了个奖杯而已。这几年父亲反倒跟随他的脚步,从拿摄影机的人变成摄影机里的人一起走绕境,父子间的话变多了。小说里陈肇仁母亲帮他做的绕境推车,现实中其实是宴平乐父亲做给他的。
我好奇,宴平路走绕境是受到爱好民俗活动的父亲影响吗?宴平乐不这么认为,“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为何喜欢民俗,他也不知道我为何走绕境,我们就莫名其妙走在同一条路上。”
信仰在荒芜中是存是灭
《起驾,回家》最终也触碰到信仰的存否:当你所相信的不如你意,信仰还存在吗?小说里有人物向妈祖许愿,祈求病榻中的母亲康复,因而走上绕境,最终却不如所愿。
宴平乐说,这其实来自绕境路上遇到的经验,“有位船长跟他太太走了好几年,某年船长跟太太都没出现,只见他儿子。儿子跟我们说他妈妈重病在医院,他向神明祈求走完妈妈就能出院。然而他出发时掷筊没过,要过大甲溪桥时就接到爸爸打来的电话,说妈妈走了。”
这该是万念俱灰的时刻,然而宴平乐说,“他爸爸在电话里告诉他‘承诺了,就要完成。’就这样,他待在大甲溪桥,等过了子时,一个人走进镇澜宫。”是信仰推动人们,还是人推动自己的力量成为了信仰?或者,这本是一体两面,无从追究因果。
我问宴平乐还会继续走吗?他说每年大家分别时都会说明年见,但他总不敢说出口,因为说了就是承诺。尽管如此,宴平乐隔年都会现身,“这些年我的体会是,绕境很神奇,这么多人朝同一个方向一起走,在这条路上全心全意。尽管我们只是在这短暂相会,等等就会分开。”
然而分开仍会在路上相见。“同队里有个老先生对我说过‘你们要把这条路传下去,以后我投胎还要来走。’”生命本是无路的,走著走著,也就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