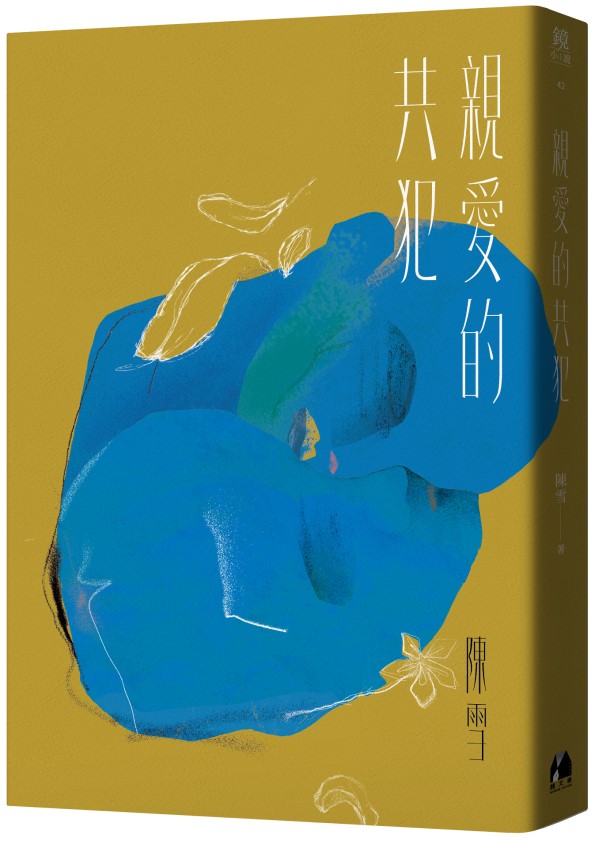写犯罪,召开一场爱的无力者大会:专访陈雪《你不能再死一次》
文|翟翱
2022-06-15
1995年,陈雪出版《恶女书》。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她还在写。酷儿先锋、台妹人妻、恋爱教主、犯罪女王,不同称号在她身上来来去去。时移事往,许多同辈小说家停笔了,文学地位同时定于一尊,但她还在写,写到让自己疑惑的地方去了。
小说家到了天命之年,却对小说有越来越多疑问。

《你不能再死一次》
陈雪 著
出版日期:2022/6/10
行过死荫之地找答案
其中一个她必须一再回答、廓清——来自他人,也是她自己的——疑问:为什么要一直写悬疑/犯罪小说?《摩天大楼》以降,接连出版《无父之城》、《亲爱的共犯》、《你不能再死一次》,用一本一本的节奏挨近犯罪小说的框架;一开始是单纯悬疑元素,接著出现侦探查案,最新的《你不能再死一次》更有了连环杀人事件。确实让人好奇,她孜孜矻矻研磨谋杀巧艺是为何?
陈雪的回答是,“为了逼近答案,”她对这答案的回答是“面对罪行我们该怎么办?”人性如迷宫复杂,也能同繁星不朽,但人很难专注探索——在这短影音、OTT夹击,长篇小说让作者跟读者都案牍劳形的时代。因此,陈雪说,需要“用犯罪小说的钩子”让读者愿意进入迷宫仰望星斗。
进入之后呢?“我想知道杀了人,会变成怎样的人?或者说杀人的动机,有没有可能杀人者到最后一刻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做?表面上这恶行很极端,但我们不也常常游走在恶行的边缘吗?去探究理解即将走向极端的人,是不是能拉回一些人?”前阵子事件视界望远镜拍到了黑洞,陈雪也在做一样的事,丢出犯罪小说的钩子到深不见底的地方,悄声问,还有人在这里吗?
从“纯文学”出发写悬疑犯罪,陈雪是孤独的。“写《摩天大楼》时,有个朋友说他不懂我为何会从《迷宫中的恋人》变成《摩天大楼》,他始终没告诉我他的纳闷是什么。好友看了我后来几本小说,只说:‘你会的是我不会的。’之后也很难再讨论。有一段时间,好像朋友们都不知道我在干嘛,那段时间我也会怀疑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好像跟好朋友已经不是同一路的人了,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讨论小说创作。这种感觉让我很困惑。后来我只能告诉自己,我是在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只能靠自己摸索。”说完,陈雪想了一下又说,“可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也写罪行啊。”

▲“难道恋爱教主加犯罪女王,就会把小说家陈雪取消了吗?”这是先行者如她,从“纯文学”到类型的大哉问。陈雪写出了疑惑,也在疑惑中自我辩证答案。(图/镜文学)
犯罪的美丽新世界
不过这句补充透露当我们讨论纯文学跨足类型,必须很小心,稍不注意就会落入谁主谁次、有尊有卑的二元窘境。陈雪自己也明白,“我很怕自己有写悬疑小说是在降低自己的感觉,相反的,我是在写悬疑/犯罪时才发现小说的边界。”
“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类型或犯罪往往被看轻,那它为何很难写?我自认是专业小说家,还是觉得很难,甚至不断问自己为何要写这个,我到底适不适合写?这让我思考,答案或许在小说自身。类不类型、纯不纯文学是小说方法的不同。”
“所以问题是,到底是什么限制了我们去写(犯罪小说)?”这或许是访谈中这么多问句里,陈雪最渴望知道答案的。
为了写悬疑犯罪,陈雪重新学写对话。这件事过去让她焦虑,“我们习惯用风格化的叙述推动剧情,但犯罪小说需要对话。进入对话后,角色说话要有个人特色,日常的感觉,不能风格化。同时,对话不像描述,很难用漂亮的文字,只能用基本功。这提醒我戒除对文字的依赖,让文字更中性。文字不只是服务作者。”
犯罪小说仰赖的框架或者说套路,一度也是陈雪的心魔。“我知道要有套路,但常常想不落俗套,所以会陷入犹豫矛盾。”从《无父之城》到《你不能再死一次》,犯罪小说的痕迹更明显,陈雪的说法是“终于摆脱心里的包袱”。写犯罪,表面上是跨界,实际上是再发现,发现小说别有洞天,发现自己还能写,“我才五十岁欸,还有扣打,可以去学习新东西。”
回到植有桃花林的小镇
《你不能再死一次》有个华美的死亡开场,少女陈尸在盛开的桃花林中,“花瓣坠落于发著短草的地上形成一片花毯,花毯中盛开著一张少女的脸。”死亡混著花与青春,禁断的甜腻气息。不久,女主角父亲被指认是凶手。父亲被捕后自缢,她因此家破人亡,远离家乡。十四年后,同样的犯罪手法再度出现,女主角被迫回到家乡,直面桃花林中的黑暗。
相较前两本,《你不能再死一次》有侦探,有办案过程。更重要的是,有凶手——一个连续杀人犯——的模样。陈雪不讳言,写这本是她创作以来最痛苦的一次,“这本小说的最大功臣是阿早,小说来自他想到的书名,我才从这书名去想怎样的情形不能再死一次。”过程中,伴侣阿早怕陈雪写不好,不断跟她讨论,“去年五月我把初稿给阿早看,被他退稿。之后我跟阿早睡前都在讨论小说要怎么写。他以一个爱人的心情担心我写差了,两边(纯文学与犯罪)不讨好,连他都说你还要写这个吗?但我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所以这本改了五个版本。交稿后我心里只想,我不想再改一次。”
所以,写犯罪小说,除了摆落文字习惯,学习套路再反套路,陈雪还学到了一件事,“以前我觉得写小说就是一个人的事,这次的经验很宝贵,打破了我的想法。”过程中,有件事让陈雪记忆犹新,“有个段落我一直写不到位,阿早就放了徐佳莹的〈人啊〉给我听——因为我平常写作只听古典乐。我是很少哭的人,写到最后,我哭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演员,在扮演自己写的角色。这时候我才想到,过去写纯文学我不会脱离自己太远,但写犯罪不一样。”
从创作者变成自己创作的角色,这一回,还包括连续杀人犯。“我想写非一般的杀人者,琢磨这样的人的心态。以杀人者当第二主角比较少见,所以我放了很多篇幅在这角色上,因为要够曲折,够层层叠叠才能逼出罪行对人的影响,又是什么导致的。”
陈雪的创作姿态,让我想到英国作家薇儿麦克德米。同是女同志,同样书写谋杀,描摹暴行。薇儿麦克德米过去常被非议,为何要写得这么残忍呢?自称见血会昏倒,却努力在小说里杀人的她回道,女性本来就生活在危机四伏中,时时都有可能遭受侵犯。因此,女性书写犯罪更能从当事者角度感受,并度人以这感受。

▲为何持续写悬疑/犯罪?陈雪还有另一个更直觉的答案,“以前写小说像在修复自己,把自己修好了要做什么?结果是写谋杀。这个呼唤非常强烈,就像我已经准备很久了。”陈雪说自己不熬夜,努力吃得好睡得好,都是为了专注写小说。仿佛身体是一座神殿,唯小说供养。(图/镜文学)
再狂野追寻一回
回到陈雪,她更从加害者的角色出发,带给读者原来爱恨互为表里。这也回到一开始陈雪的疑惑,恋爱教主为什么一再操演犯罪?“很多读者习惯看我的脸书写恋爱故事,可是读完那三百字后,就像喝鸡汤也不会长肌肉。不被爱,不爱自己小孩,因为爱做了错误决定,或者爱怎样拯救自己,都是读小说才能有的体悟。”陈雪是小说之神钟爱的女儿,因为她仍信仰小说的力量,“小说让我们拥有无法度过的人生,透过阅读,你逐渐经历别人的人生,而被改变。即使你从小到大都待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读了很多小说,你就能穿透世界。”
因此,陈雪左手写恋爱课散文,右手写出《无父之城》是小我的爱遇到国家级暴行的下场;《亲爱的共犯》是彼此相助如珍珠项链般串链的珍贵之心;而《你不能再死一次》则是当爱被误译的悲剧。
陈雪坦言,一开始不大喜欢恋爱教主跟犯罪女王这类标签,“但后来我觉得也满酷的,而且它们是有共通的,都是关于爱的想像。小说里,我尽量让读者可以找到一个站立的地方,不要站在流沙上。回过神,人会发现自己是可以穿越这些残酷无情的。”
一手写恋爱,一手写不被爱,需要精巧而调节的平衡感。陈雪说,现在的稳定生活,给她这样的写作力量。“以前的我没办法达到这种平衡,因为以前我就是谈恋爱与无止尽的幻灭,不断找下一个人。我会想,难道人只能互相勾引,狂爱后背叛、分离吗?难道爱情没有另一种可能吗?这样想才意识到,我以前的生活也是一个套路啊,我用现在的生活证明了,人可以反自己的套路。”
访问前夕,陈雪以《亲爱的共犯》获书展小说奖大奖。我问她有何感受,陈雪回答,得奖让她觉得好像可以再写一本;写犯罪,终于感觉自己不是出界了,而是在拓展身为小说家的边界。
边界落在哪?小说家其实走过。陈雪说了一段故事,“前阵子《恶魔的女儿》重出,我才发现里头都是对话,阿早就说不是你不会写对话,只是忘记了。我想对啊,如果世界上没有我的价值,我应该要自己定义。当初《恶女书》连出版都差点没办法,为什么我到了五十岁,写东西要绑手绑脚?我应该再大胆一次。”
这次访陈雪,是我听过受访者丢出最多疑问的一次,也是透过疑问获得最多力量的一次。我想起罗贝托博拉纽一首关于侦探的诗,遥远回应了陈雪不断探问的小说的边界:“我梦见迷失的侦探/在阿诺菲尼夫妇家的凸镜里: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恐怖模型。”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视角,我们的所惧怕的,都构成了小说家的边界。陈雪是博拉纽梦见正寻寻觅觅的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