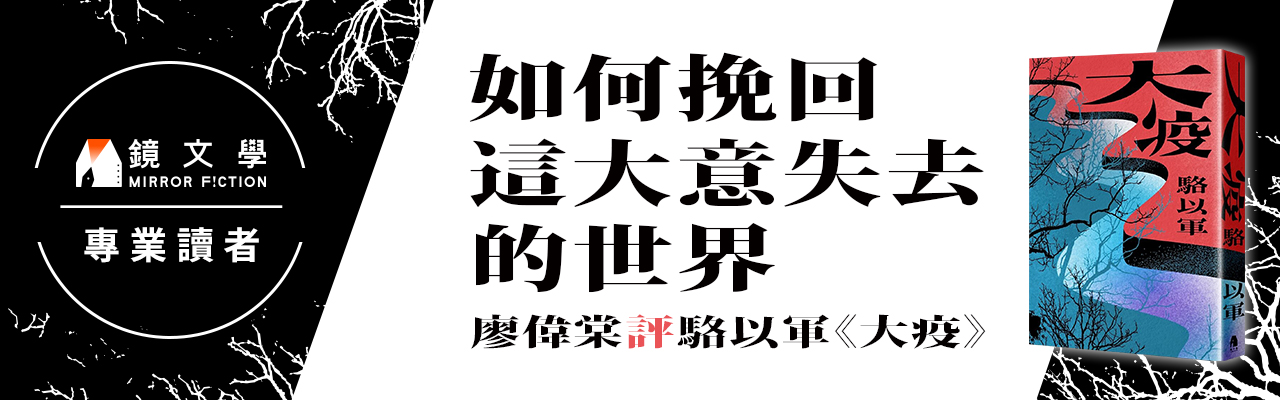如何挽回这大意失去的世界——廖伟棠评《大疫》
文|廖伟棠
2022-09-20
《大疫》面世的时候,久未在脸书露面的骆以军发布了一段短短的打书文,以他一贯的玩笑话开始,他说告知妻儿《大疫》出版的消息,小儿子说:“是关于粗心大意的故事吗?”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场惊世大疫,很可能真的出自某个人的粗心大意。但粗心大意不是偶然的,人类文明/反文明的发展也来自一连串停不下来的粗心大意,殊不知这都是人性注定的,或曰灵感或曰疏漏,或曰求生意志或曰自毁欲望,都是硬币两面,硬币如何落下便有不同的结局。

骆以军 著
出版日期:2022/8/5
骆以军无疑深解此理,因此他建立《大疫》里人歌人哭的末日后桃花源时,一边是穷尽心力巧夺天工(他在文字上下的功夫对应了溪谷主人在制陶和冶园的“变态”执迷),但另一边是率性繁衍,听凭造化之力对“文明”变形、锤锻,小说结构和线索之类的破坏来乱一如书中回溯的“疫前”世界,充满无来由的暴力、恶意与荒诞。根本不需要什么大疫,我们一直是这个世界的病毒,精妙非常,暴虐非常。
写下“人歌人哭”,我是想到了杜牧的《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这样一种对文明盛衰的泰然任之,略带悲悯,很东方,相对于《十日谈》的辛辣肉感。可以说《大疫》是一部杜牧执笔的《十日谈》,这并不矛盾,别忘了杜牧还有春风十里扬州路的轻狂艳丽,那也是《大疫》叙事者稍不能忘的三生前事。
但作为受益于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代,骆以军没有忘记西方正典邪典给他的馈赠。作为故事的其中一个潜文本,常常被提及的是伯格曼的电影《第七封印》和《芬妮和亚历山大》——后者结尾念白那句斯特林堡之“万事皆可发生,时间空间并不存在,在现实脆弱的框架之下,想象如纺线交织着新的图案”完全可以看作骆以军一以贯之的创作追求。我们的文青营养剂想不到在这样的地步——小说中万物凋零、文明寂灭前夕——爆发衍生,成为救赎。
骆以军对这类救赎,半推半就。他可以决绝:“我们早就不是人类了。只是一些无限打开窗口的幻影,没有东西不能被羞辱、传输、修改、说谎、冒用。这是真的发生了。‘我们只是一个很烂的剧作家写的,面孔模糊,滴哆走著就融化的角色’。不,连‘角色’都不是,是一种‘人类’已不在了,但在空气中无所不在,如烟飘散的‘戏’。这时我们很久没有稍停顿一瞬,愣想一下:什么是戏? ”
“什么是戏?”——虚无增值一万倍,也依然是虚无,反过来说,文明削弱一万倍,也依然是文明的幽光。可以揣测造就骆以军动笔《大疫》的其中一幕,和同样震撼我的一幕相似:那就是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地中海数国在瘟疫大爆发时的迅速沦陷,义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的死亡数字几何级增长之际,梵蒂冈教宗方济各在傍晚雨中来到圣伯多禄大殿前,独自祈祷求主垂怜饱受痛苦的人类。那一刻,方济各与伯格曼的骑士形象恍惚重合,他其实是在跟死神对弈,以求苟延文明。
骆以军举的例子,是卢梭的画《入睡的吉普赛女郎》“很久以来,(那已经十几年了)我都挂在网路上,快速翻跳朝生暮死的讯息,但那个停住的时刻,那么静谧、幸福、哀伤,纯粹就是那幅画的美。可能就是那一年,人类的悲惨,或那近乎一百年全白贵的,如同回到一战前的,对他人的大括弧之贬低、羞辱、仇恨,这应当深深伤了我这一代,曾经被‘世界’的文明、艺术、思想启发,追梦者的心。 ”
作为文明之子,骆以军不甘,因此无论溪谷主人和老和尚等多么“出世”,他终究是入世而非厌世,执著而非虚无的,在小说后半段痛斥历史时他简直是愤世的。同时,骆以军向著他小说里的人物、故事,绝不轻易放过一个人的命运任其流落虚空,均浓墨重彩渲染之,大有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勇猛与悲壮,但地狱在乎一念,这一念何来?
《大疫》一发,其启万端,若只取一,那就是香港——香港来的那个女子“安”——那个香港的小寡妇。这当然不是我自己的偏心,这也是骆以军的偏心,这个女子(我怀疑我认识她的本体)曾出现过在他其他叙事里面,但这一次最为痛彻心扉。是因为加上了香港本身的悲剧吗?他们相识的十年前的香港,如今不但在政治的角力,在若即若离的异乡人的生命错位中也败坏下去了。
然后的香港未亡人,难道可以作为隐喻理解吗?无论如何,她成为这部小说的最沉重的钥匙。“她是这溪谷中的‘故事之夜’中,意外成了所有故事的女王⋯⋯就像是深海中无数艘沉没的船只,她就是那艘让人唏嘘、慨叹的铁达尼号。她似乎裹胁了大多人世本来的美好梦想、一只一只冒出银光大气泡下沉的铁箱、一层又一层的失落之物 ”
不,铁达尼号?这难道不是珍宝海鲜舫?或者鲸落——“我们之所以能在此有缘相聚,或是,我能如坠五里雾、螺旋锥下跌,进入这‘馀生’,全是她那良善的念头,一瞬之光幻造出来的这绿光盈满之溪谷? ”——或者这是安(不安)的方舟,还是末日馀光之中哭笑前行的疯人船?
骆以军的耿耿于怀是一回事,而“D-DAY 来临,全部人类的大写时间全终结之时,香港曾发生过的那一切,并来不及给一个公义、人类之光、救赎、甚或神之判决的什么。”则写出了我的耿耿于怀。世界会因为对一个人的辜负而报应万物吗?神会因为我们对一座城市的辜负而报应世界吗?骆以军安排了安的死亡是身处疫情最严重时期的西班牙,把个人的耿耿和文明的绝灭牵手了,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神不会,但小说之神可以。
小说之神,可大可小,在《大疫》里他毫不掩饰自己就是一个万能的、所向披靡的病毒这一狂想。这是狂想,也是狂悲。“他要把她,不,和她的美丽年轻裸体拥抱在一起的这衰老的自己,这一段画面,封印、隔绝、藏匿在他的‘在一切之外的房间’”——悲哀莫过于执迷,“他便已预知了这个分崩离析的时光之歌的无情,不,不是她无情,而是这样的向量,四面八方、里面外面,每一个延伸出去的触突,都被打开了基因开关,像迷宫回廊成千上万依序排列的小小胎儿,突然都开了眼。”
——但这无数缘起缘灭,惊心动魄又如何?“你在那个时刻,给了那女孩一个绵绵、像雨季、湿润山林雾气的、扑朔迷离、上万只音叉共振的‘情’:‘女孩别怕,我们都在这里。’这是所有听故事者,给那些因生命的凹洞、悲剧、不能承受的遭遇,而隐约将形成‘故事’者,最大的安慰。”除了小说里的女子,我还感谢骆以军为张紫妍们、林昭们抱冤,这不仅仅是一个贾宝玉情结,也是对文学最大的信任、冀望。
“我想说的是‘爱’。是的,‘爱在瘟疫时’里的那个,像人子耶稣凌波走在水上,在一切空洞、死灭、下沉的全景上,奇迹似走动的那个字,‘爱’。”很难想像这样传教者式的话从魔鬼骆以军笔下写出。但正是这爱与瘟疫的螺旋式交配,衍生了人类之舞,一如叶慈《在学童中间》里所写的:
果树啊,根柢雄壮的花魁花宝,
你是叶子吗,花朵吗,还是株干?
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灼亮的眼神!
我们怎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
小说走向结束前,因为现实世界里疫情得到控制,以及始终悬宕在本岛上空的战争的阴晴变幻,使得本来是末日小说的《大疫》,意外变成了架空历史小说。结尾又从架空小说猛然一跃进入某种元科幻的境地,以恍兮惚兮的身分迷失去反思整个宇宙的存在,实际上是本体论式的哲学沈思的图像化。骆以军的想像力驾驭这一切绰绰有馀,他又一次挑战了他的假想敌刘慈欣。
不过他的悲悯决定了他和刘慈欣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在他把病毒角色分享给每一个值得同情、值得珍惜的人(甚至有一章给予大家都不屑再写的老兵)的时候,这场大疫就注定和现实的大疫不同,它实际上是大翼、大忆、大义、大熠等等混合而成的一场“大呓”,它只属于那个在六十年代台北仓皇的微光中走失的孩子,他要用数十年的书写去把自己的、文明的本来面目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