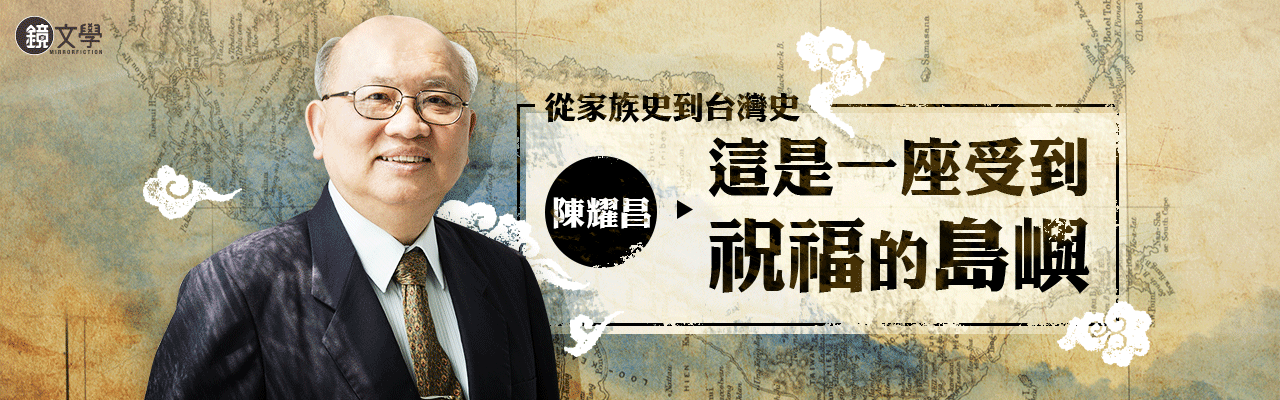【作家特写】从家族史到台湾史 陈耀昌:这是一座受到祝福的岛屿
文|陈琡分
2019-02-18
 立即阅读:《狮头花》
立即阅读:《狮头花》
追索家族血脉的故事,是陈耀昌写作的起点。
他自医学研究半路出家写小说,为的是当初听说陈家祖上有个「荷兰嬷」。写著写著,荷兰嬷究竟有无,于今对他而言已不那么重要。他有更大的心愿──希望今年(2019),我们的政府官员能够去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找出一份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由台湾原住民头目卓杞笃与美国驻厦门总领事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 1830-1899),所签下的约定书。
那是十九世纪中期,发生在恒春半岛的事。一八六七年,美国商船罗妹号(Rover)于垦丁一带触礁,船员们登陆避难,却不幸遭当地排湾族原住民袭击。船员家属辗转委托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李仙得前往交涉,促成了李仙得与当时「下瑯峤十八社」总头目卓杞笃会面,协调原住民日后协助船难者的允诺。
一八六九年二月,两人再次见面时,卓杞笃要求将先前的口头约定落成文件,成了台湾第一份由原住民与外国签订的外交条约──据信这份文件目前仍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这段历史,则成了陈耀昌「台湾花系列」首部曲《傀儡花》的上演舞台。
自医跨文 习惯埋头找资料
《傀儡花》之后,是《狮头花》。接续《傀》书写的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年, 重现一八七五年屏东大龟文王国与清朝淮军之间,那场如今早已被岛民淡忘的「狮头社战役」。厚墩墩两部钜作,出版时间相隔不过一年余;此前他还有小说处女作《福尔摩沙三族记》,一出手就是大长篇。说起写作过程,陈耀昌最常挂在嘴上的,无非是他四处踏查田调时所碰上的种种巧合,以及那句总是被他用来作为结论的「如有神助」。
「每次人家提到我写小说,都说我不务正业。我要特别强调,我才没有不务正业。我可是很认真在做我的医学教授。」陈耀昌半开玩笑地亮出卫福部颁发的奖章──这位全台首屈一指的血液肿瘤内科名医兼台湾细胞医疗先驱,执笔写起小说,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陈耀昌开始写小说后,许多人开他玩笑说他「不务正业」,其实他另一个身分是血液肿瘤内科名医兼台湾细胞医疗先驱。
陈耀昌开始写小说后,许多人开他玩笑说他「不务正业」,其实他另一个身分是血液肿瘤内科名医兼台湾细胞医疗先驱。
「很多人都问我怎么开始写作的。我五十岁之前只有写过两次文章:一次是小学五年级的全省作文比赛,我得了第九名,那是我唯一和写作有关的奖项;第二次是大学时,我担任台大医学院学生院刊《青杏》社长。这是我少数与写作沾得上边的时候。」讲起来都是相当久远的事。
二○○三年二月,陈耀昌受时任中央社副社长的曾嬿卿邀请,在《财讯》开了生技专栏,一写就是三、四年,是陈耀昌固定发表文字的起点。二○○四年,一次回台南老家扫墓,叔叔告诉他,陈家在台湾第一代的查某祖是「荷兰嬷」。「我就想:我自己是做基因研究的,怎么不试著看看从资料证明我是荷兰人(的后代)?」
有了专栏「练笔」的基底,加上毕生从事医学研究,早已培养出埋首文献资料的无限耐心与功力;惊人的记忆力,更让任何蛛丝马迹烙印在陈耀昌的脑海里,举凡人名、照片、时间日期,近乎过目不忘,必要时得以串连──凡此种种,都为陈耀昌自医跨文的锻炼做足了准备。
二○○九年八月二十九日,陈耀昌人在首尔,半夜三、四点睡不著,干脆起身写下《福尔摩沙三族记》第一章。「我第一行怎么写你知道吗?我写:『三到五万字,中短篇小说。』」起于叔叔不经意的一次谈话,让陈耀昌从家族的追寻,爬梳一六二四年荷兰人来台后,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千丝万缕,最后成了浩浩荡荡的长篇。虽然没能真正证明自己的血脉,然作品出手掷入文坛,却是一鸣惊人。「我的目的是写我祖先的故事。后来幸运得了奖,想说不要变成一书作家,这样太丢脸了。就继续写吧。」他说著说著,又是哈哈一笑。
重视踏查 藉此呈现多元史观
写的虽是小说,然陈耀昌非常重视踏查;亲临现场为他带来的冲击,不仅是他创作时源源不绝的灵感,更是他无法停笔的驱动力。许是自身医学领域的间接影响,陈耀昌的小说主题,特别著眼于台湾历史上族群间的冲突与融合。如同他在另本著作《岛屿DNA》所声明的主张:台湾人(种族)很「混」,且早已「混」得都相同。「假如我们从一六六一年郑成功来台算起,到现在三百五十几年。往上回溯,经过了十二代或十三代,一个人有几个祖先?答案是2048或4096。现在的你的DNA,只是那里面一个人的,你要怎么证明不同?」这是陈耀昌不时倡导族群和谐的论点基础。
 写的虽是小说,陈耀昌非常重视踏查,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点,再远他都跑去现场。图为原建于光绪三年(1877),位于北势寮的「淮军祠」(不知何时改名为白军营),埋有约四百名未参加「狮头社战役」即已病逝台湾的淮军。
写的虽是小说,陈耀昌非常重视踏查,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点,再远他都跑去现场。图为原建于光绪三年(1877),位于北势寮的「淮军祠」(不知何时改名为白军营),埋有约四百名未参加「狮头社战役」即已病逝台湾的淮军。
台湾是移民社会,随时有人来来去去;台湾人的「混」,是地理与历史造成的必然。也因此,陈耀昌认为,读台湾史,需如陈寅恪所说:要有「了解之同情」。
陈耀昌写《傀儡花》,写《狮头花》,写原住民、汉人、清朝淮军之间的纠葛,只要是能查找到的地点,哪怕可能只是一座破败的小庙、偏远的孤坟,再远他都跑去现场,试图感受空气中遗留下的氛围。「我们常说汉人欺压原住民,或说原住民袭击汉人,其实不能这样讲。一边是冒死过来求生存,一边是受到侵犯。但这就是移民社会的无奈。」清朝实施海禁,中国沿海居民迫于生计,只得冒死渡过「黑水沟」,所谓「六死三留一回头」,成功率只有三成。「大家都有为了求生存的不得已,不然要怎么活下去?」
「所以我才强调『多元史观』,特别像我们这样的移民社会更加需要。要两边互相体谅。但这很难。」陈耀昌认为,要解决族群问题,必须先相互了解历史。毕竟各有处境,端看各自理解的角度。
然这样不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吗?「你要说是,也许吧。但要这样才能族群和谐啊。」人生在世,谁都不过图个安身立命,但能不能在互知互谅的前提下,做出最大的转圜?「台湾的族群混杂是事实。族群当中,我们可以分出各自的文化,那是多元;而族群的确有人数多寡,我要强调的是『同舟共济大和解』,包括一九四九年过来的人也一样。用俾斯麦的话:愚者向经验学习,智者向历史学习。历史上很多战争都是因为小事情擦枪走火,在这个时代,我们更要避免同样的状况再发生。」
小说化历史 补足台湾史空洞之处
 《狮头花》企图重现一八七五年屏东大龟文王国与清朝淮军的「狮头社战役」。图为位于台东达仁乡的大龟文王国标示。
《狮头花》企图重现一八七五年屏东大龟文王国与清朝淮军的「狮头社战役」。图为位于台东达仁乡的大龟文王国标示。
纵使陈耀昌后来的书写,已与追寻家族血脉无关,然他依旧孜孜不倦,要说他转而追寻「台湾史的血脉」,也无不可。「我自认我写的是小说化的历史,不是历史小说。台湾史有太多被误解的、空洞的地方,我希望我可以补上。就像吴密察说我是『另类的历史书写』。他承认我写的是历史,不是凭空编造的小说。」以小说为手段,替「如何理解台湾历史」下一帖药方,正是陈耀昌的目的所在。
「台湾一直是被上天眷顾著的。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大规模战争,土地下的冤魂,为数甚少。当然要去理解对方、对不同立场的人感同身受,是一件困难的事;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像我们台湾这样,无论从民族、历史、地理等观点来看,都这么复杂。但我们是很特殊的。这是历史给我们的优势。」即使每一段台湾史读来、写来,处处都是艰辛困苦,陈耀昌依旧怀抱乐观,「我一直认为,我们是被祝福的。Be blessed。」